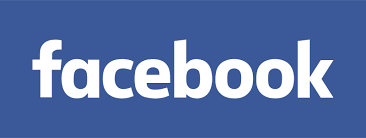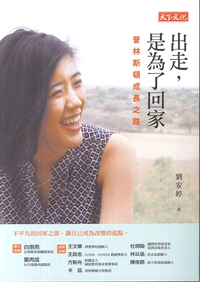гҖҖгҖҖзө•жңӣпјҢжңғеӮіжҹ“гҖӮеӢҮж°Јд№ҹжҳҜпјҒ
гҖҖгҖҖдёҖеҖӢй Ӯи‘—гҖҢиіҮе„Әз”ҹгҖҚе…үз’°гҖҒ
гҖҖгҖҖд»Ҙе…ЁйЎҚзҚҺеӯёйҮ‘йҖІе…ҘзҫҺеңӢеҗҚж Ўзҡ„еҸ°зҒЈеҘіеӯ©пјҢ
гҖҖгҖҖеҚ»иў«иіӘз–‘гҖҢеҰіжҳҜжҖҺйәјиҖғдёҠжҷ®жһ—ж–Ҝй “зҡ„пјҹгҖҚ
гҖҖгҖҖжӢҡе‘Ҫжғіж“ йҖІгҖҢй…·гҖҚжңӢеҸӢеңҲпјҢеҚ»йҒәиҗҪдәҶжңҖзңҹеҝғзҡ„еҸӢиӘјпјӣ
гҖҖгҖҖеҲқеҡҗжҲҖж„ӣж»Ӣе‘іпјҢеҚ»еңЁж„ӣдёӯеӨұеҺ»иҮӘжҲ‘пјӣ
гҖҖгҖҖеҠӘеҠӣжғіеңЁзҫҺеңӢй—–еҮәдёҖзүҮеӨ©пјҢеҚ»зҷјзҸҫиҮӘе·ұзөӮ究дёҚеұ¬ж–јз•°й„үпјӣ
гҖҖгҖҖйқһжҙІиҝҰзҙҚгҖҒзҫҺеңӢзӣЈзҚ„гҖҒжө·ең°гҖҒе·ҙй»ҺгҖҒжҹ¬еҹ”еҜЁгҖҒж—Ҙе…§з“Ұ……
гҖҖгҖҖйӣўй–Ӣ家й„үж„ҲйҒ пјҢеӣһ家зҡ„жёҙжңӣж„Ҳеј·зғҲгҖӮ
гҖҖгҖҖеҘ№зҡ„жҢ«жҠҳпјҢжІ’жңүе°‘йҒҺпјҢ
гҖҖгҖҖеҘ№зҡ„жҲҗй•·пјҢе……ж»ҝз„Ұж…®пјҢ
гҖҖгҖҖеҘ№зҡ„дәәз”ҹи·ҜпјҢд№ҹйқһдёҖеёҶйўЁй ҶпјҢ
гҖҖгҖҖеҘ№ж”ҫжЈ„зҫҺеңӢдәәдәәзЁұзҫЁзҡ„й«ҳи–Әе·ҘдҪңпјҢ
гҖҖгҖҖеӣһеҲ°еҸ°зҒЈжҠ•иә«еҒҸй„үж•ҷиӮІпјҢ
гҖҖгҖҖиө°дёҖжўқиүұиҫӣзҡ„и·ҜпјҢ
гҖҖгҖҖеҘ№ж“Ғжңүзҡ„пјҢеҸӘжҳҜеӢҮж°ЈгҖӮ
е°Ҳж–ҮжҺЁи–Ұ
гҖҖгҖҖзҷҪеҙҮдә®в”ӮеҸ°зҒЈеҘ§зҫҺйӣҶеңҳи‘ЈдәӢй•·
гҖҖгҖҖи‘үдёҷжҲҗв”ӮеҸ°еӨ§йӣ»ж©ҹзі»еүҜж•ҷжҺҲ
еҗҚдәәжҺЁи–Ұ
гҖҖгҖҖзҺӢж–ҮиҸҜв”ӮеӨўжғіеӯёж ЎеүөиҫҰдәә
гҖҖгҖҖзҺӢж”ҝеҝ в”ӮSUPERгҖҒPOWERж•ҷеё«зҚҺгҖҒеё«йҗёзҚҺеҫ—дё»
гҖҖгҖҖж–№ж–°иҲҹв”ӮиІЎеңҳжі•дәәиӘ иҮҙж•ҷиӮІеҹәйҮ‘жңғи‘ЈдәӢй•·
гҖҖгҖҖеҚЎгҖҖиҢІв”Ӯжҷ®жһ—ж–Ҝй “еЁҒзҲҫйҒңеңӢйҡӣиҲҮе…¬е…ұдәӢеӢҷеӯёйҷўж•ҷжҺҲ
гҖҖгҖҖжқңжҳҺзҝ°в”ӮеңӢйҡӣдё–з•Ңеұ•жңӣжңғдәһжҙІеёӮе ҙиІ иІ¬дәә
гҖҖгҖҖжһ—д»Ҙж¶өв”ӮзӨҫдјҒжөҒеүөиҫҰдәә
гҖҖгҖҖйҷідҝҠжң—в”Ӯеӯ©еӯҗзҡ„жӣёеұӢеүөиҫҰдәә
гҖҖгҖҖ(дҫқ姓ж°ҸзӯҶз•«жҺ’еҲ—)
гҖҖгҖҖзңӢе®үе©·зҡ„еӨ–иЎЁпјҢдёҚжңғжғіиө·гҖҢжөҒжөӘгҖҚжҲ–гҖҢеӯӨзҚЁгҖҚгҖӮдҪҶеҘ№зҡ„ж•…дәӢпјҢе……ж»ҝдәҶйҖҷе…©еҖӢе…ғзҙ гҖӮжөҒжөӘпјҢдёҖж–№йқўиЎЁзҸҫеңЁзҷ»ж©ҹиӯүе’ҢиЎҢжқҺз®ұпјҢеҘ№еҺ»дәҶиҝҰзҙҚгҖҒжө·ең°гҖҒж—Ҙе…§з“ҰгҖӮеҸҰдёҖж–№йқўиЎЁзҸҫеңЁеҘ№дёҚж–·жҺўзҙўз”ҹе‘Ҫзҡ„ж–№еҗ‘гҖӮеҘ№е•ҸдәҶиҮӘе·ұеҫҲеӨҡж·ұеҲ»зҡ„е•ҸйЎҢпјҢеҢ…жӢ¬пјҡйқһзҮҹеҲ©зө„з№”пјҢжңғдёҚжңғд№ҹеҸӘжҳҜиҲ’йҒ©еңҲпјҹиҮіж–јеҘ№зҡ„еӯӨзҚЁпјҢдёҖж–№йқўиЎЁзҸҫеңЁж„ӣжғ…зҡ„еӨұиҗҪпјҢеҘ№еҲҶдә«дәҶдәҢеҚҒжӯІзҡ„еҲқжҲҖпјҡпјүеҸҰдёҖж–№йқўиЎЁзҸҫеңЁеҘ№еҒҡеҮәеҫҲеӨҡдёҚеҗҢзҡ„йҒёж“ҮпјҢеҢ…жӢ¬Teach For TaiwanгҖӮйҖҷеҖӢж•…дәӢжҲ‘жңҖе–ңжӯЎзҡ„з•«йқўпјҢжҳҜе®үе©·дәҢв—Ӣв—Ӣе…«е№ҙ第дёҖж¬ЎеҲ°жҷ®жһ—ж–Ҝй “жҷӮпјҢеңЁзҙҗзҙ„ж©ҹе ҙжүҫжҺҘй§Ғи»Ҡзҡ„е ҙжҷҜгҖӮ經йҒҺдёҖз•ӘжҠҳйЁ°пјҢгҖҢи»ҠеӯҗдёҖдёҠи·ҜпјҢжҲ‘дҫҝдёҚж”ҜжҳҸзқЎеңЁеӘҪеӘҪзҡ„еӨ§и…ҝдёҠгҖӮгҖҚе®үе©·гҖҒжҲ‘еҖ‘гҖҒеҸ°зҒЈпјҢйғҪеңЁжөҒжөӘпјҢд№ҹе°Үй«”жңғжӣҙеӨҡеӯӨзҚЁгҖӮе°ұи®“е®үе©·зҡ„ж•…дәӢпјҢжҲҗзӮәжҲ‘еҖ‘з–ІжҶҠжҷӮзҡ„ж”ҜжҹұгҖӮв”Җв”ҖзҺӢж–ҮиҸҜпјҢеӨўжғіеӯёж ЎеүөиҫҰдәә
гҖҖгҖҖжҲ‘е…¶еҜҰжІ’жңүзңҹжӯЈиӘҚиӯҳе®үе©·гҖӮиҰӢйқўдёҚи¶…йҒҺдә”ж¬ЎпјҢе°Қи©ұж¬Ўж•ёеұҲжҢҮеҸҜж•ёпјҢеҚідҫҝз¶Іи·ҜжҲ–еӘ’й«”е ұе°ҺпјҢжҲ‘д№ҹеҫҲйӣЈжңүе®Ңж•ҙзҡ„жҷӮй–“д»”зҙ°й–ұиҒҪгҖӮжҲ‘е”ҜдёҖзҹҘйҒ“зҡ„пјҢжҳҜеҘ№еҸӘиҠұдәҶдёҚеҲ°е…©е№ҙпјҢе°ұеҲқжӯҘе®ҢжҲҗжҲ‘еҠӘеҠӣдәҶеҚҒдёғе№ҙзҡ„дәӢгҖӮйҖҷеҚҒдёғе№ҙпјҢжҲ‘еңЁеҒҸй„үзӘ®зӣЎдёҖеҲҮеҠӘеҠӣпјҢи©Ұең–и§ЈжұәеҸ°зҒЈж•ҷиӮІй«”еҲ¶е…§з„Ўжі•и§ЈжұәпјҢеҚ»д№ҹз„ЎжҜ”йҮҚиҰҒзҡ„дәӢпјҢзӣ®еүҚжҲ‘е’ҢжҲ‘зҡ„еңҳйҡҠеңЁжҲ‘еҖ‘зҡ„зҸҫе ҙдјјд№ҺеҲқжӯҘи§ЈжұәдәҶеӣ зӮәеғөеҢ–зҡ„ж•ҷиӮІз·ЁеҲ¶иҖҢйҖ жҲҗжӯ»ж°ҙиҲ¬зҡ„её«иіҮеӣ°еўғв”Җв”ҖиҰҒиө°зҡ„и©Іиө°зҡ„иө°дёҚдәҶпјҢжғійҖІи©ІйҖІзҡ„йҖІдёҚдҫҶгҖӮиҖҢе®үе©·пјҢдёҖеҖӢдёҚеҲ°дәҢеҚҒдә”жӯІзҡ„е°ҸеҘіз”ҹпјҢжІ’жңүж•ҷиӮІе°ҲжҘӯиғҢжҷҜпјҢжІ’жңүе®ҳж–№еҜҰйҡӣеҘ§жҸҙпјҢеҚ»дёҖи…”зҶұиЎҖзҡ„жғіиҰҒеҚ”еҠ©и§ЈжұәеҸ°зҒЈеҒҸй„үеӯёж Ўзҡ„её«иіҮе•ҸйЎҢгҖӮеҘ№е·Із¶“й–Ӣе§ӢпјҢдёҰдё”жңүдәҶеҘҪзҡ„еҮәзҷјпјҢTFTжӯЈиӘҚзңҹеүҚйҖІпјҢеҚідҫҝдёҖе ҶдәәеҝғеӯҳиіӘз–‘в”Җв”Җзү№еҲҘжҳҜй«”еҲ¶е…§зҡ„е°ҲжҘӯеё«иіҮеҹ№иӮІзі»зөұгҖӮдҪҶпјҢеҸҲеҰӮдҪ•пјҹеҘҪеҘҪзңӢзңӢе®үе©·зҡ„жӣёпјҢжҲ–иЁұжҲ‘еҖ‘е°ұжңғзҹҘйҒ“пјҢйҖҷеҖӢеҫһз•°й„үеӣһдҫҶзҡ„е°ҸеҘіз”ҹпјҢжҳҜеҰӮдҪ•жңүиғҪиҖҗзҡ„жғіиҰҒзӮәеҸ°зҒЈеҮәзҷјгҖӮв”Җв”ҖзҺӢж”ҝеҝ пјҢSUPERгҖҒPOWERж•ҷеё«зҚҺгҖҒеё«йҗёзҚҺеҫ—дё»
гҖҖгҖҖе…©е№ҙеүҚпјҢзӮәдәҶеӨҡдәҶи§ЈејұеӢўе®¶еәӯпјҢжҲ‘иҲҮе№ҫдҪҚеҘҪеҸӢжӢңиЁӘеҫҲеӨҡиӘІиј”е–®дҪҚпјҢеҢ…еҗ«е®үе©·зҲёеӘҪзҡ„жһ—жҘӯз”ҹеҹәйҮ‘жңғгҖӮеңЁз¬¬дёҖж¬ЎгҖҢзӨҫжңғеүөжҘӯ家жҲҗй•·зҮҹгҖҚеҫҢпјҢжүҚиӘҚиӯҳе®үе©·пјҢйҖҷдҪҚи®“еҘ№зҲёеӘҪеј•д»ҘзӮәжҰ®гҖҒеҸҲж“”еҝғзҡ„еҜ¶иІқеҘіе…’гҖӮдёҖй–Ӣе§ӢпјҢи·ҹе®үе©·зҡ„й—ңдҝӮеҜҶеҲҮеҸҲз–ҸйӣўгҖӮеҜҶеҲҮжҳҜеӣ зӮәжҲ‘еҖ‘еҹәйҮ‘жңғе№ҫдҪҚе№ҙиј•еӨҘдјҙжҳҜTeach For Taiwanеҝ—е·ҘпјҢд»–еҖ‘еёёеңЁжҲ‘еҖ‘иҫҰе…¬е®Өй–ӢжңғпјҢеёёеёёиҰӢйқўпјӣз–ҸйӣўжҳҜеӣ зӮәе®үе©·еӨӘе„Әз§ҖгҖҒеӨӘдә®йә—гҖҒиҰӢйҒҺеӨӘеӨҡдё–йқўпјҢжҲ‘дёҚеӨӘзўәе®ҡеҘ№жҳҜеҗҰдёӢе®ҡжұәеҝғиҰҒеүІжҚЁе……ж»ҝеёҢжңӣгҖҒеүөж„Ҹзҡ„дё–з•ҢиҲһеҸ°пјҢиҖҢеӣһеҲ°еҫҲжӮ¶гҖҒеҫҲиІ йқўжғ…з·’гҖҒи¬ӣ究жҺ’иіҮи«–иј©зҡ„еҸ°зҒЈгҖӮеҘ№з«ҹ然зҺ©зңҹзҡ„пјҢеӣһдҫҶдәҶгҖӮйҷӨдәҶеҘ№иҮӘе·ұзҡ„еӢҮж°Ји·ҹж„ӣеҝғеӨ–пјҢTFTзҡ„е…¶д»–еӨҘдјҙжҳҜеҪұйҹҝеҘ№еӣһдҫҶзҡ„жңҖеӨ§еҺҹеӣ гҖӮйҖҷдәӣеӨҘдјҙйғҪжҳҜгҖҢдәәз”ҹеӢқеҲ©зө„гҖҚпјҢеҚ»з”ҳйЎҳйҒёж“ҮдёҖжўқдәәз…ҷзЁҖе°‘зҡ„и·Ҝиө°гҖӮж„ҲиӘҚиӯҳд»–еҖ‘пјҢжҲ‘ж„ҲиӘҚзңҹзңӢеҫ…д»–еҖ‘пјҢж…ўж…ўеҫһй•·иј©и®ҠжҲҗжңӢеҸӢпјҢжңҖиҝ‘еҸҲеҫһжңӢеҸӢи®ҠжҲҗзІүзөІгҖӮжҲ‘еңЁд»–еҖ‘иә«дёҠзңӢеҲ°еҸ°зҒЈзҡ„еёҢжңӣгҖӮв”Җв”Җж–№ж–°иҲҹпјҢиІЎеңҳжі•дәәиӘ иҮҙж•ҷиӮІеҹәйҮ‘жңғи‘ЈдәӢй•·
гҖҖгҖҖе°ҚжҲ‘иҖҢиЁҖпјҢе®үе©·дёҖзӣҙйғҪжҳҜеҖӢе…ёзҜ„еӯёз”ҹгҖӮжҳҺйЎҜзҡ„пјҢеҘ№жҘөз«Ҝзҡ„иҒ°жҳҺгҖҒе–„иЁҖпјҲиҮіе°‘дёүеҖӢиӘһиЁҖпјүгҖҒжңүжҙ»еҠӣгҖҒеҸҲжңүеүөжҘӯ家зІҫзҘһгҖӮеңЁжҺҘдёӢдҫҶзҡ„е№ҫе№ҙпјҢTeach For TaiwanеҫҲжңүеҸҜиғҪжңғжҲҗзӮәдёҖеҖӢйқһеёёйҮҚиҰҒзҡ„зө„з№”гҖӮжІ’йҢҜпјҢдёҖеҖӢйҖҷйәје№ҙиј•зҡ„дәәиғҪеӨ еңЁйҖҷйәјзҹӯзҡ„жҷӮй–“иЈЎжҲҗе°ұйҖҷйәјеӨҡпјҢжҳҜдёҖ件дёҚеҸҜжҖқиӯ°зҡ„дәӢжғ…гҖӮдҪҶе®үе©·зңҹжӯЈдёҚеҮЎзҡ„ең°ж–№пјҢеңЁж–јеҘ№зёҪжҳҜеҰӮжӯӨз”Ёеҝғзҡ„еҸҚжҖқеҘ№з”ҹе‘Ҫзҡ„ж—…зЁӢгҖӮжҲ‘еёҢжңӣеҘ№зҡ„ж•…дәӢиғҪжҝҖеӢөе…¶д»–иҒ°жҳҺгҖҒе°ҚзӨҫжңғжңүиІ ж“”зҡ„еҸ°зҒЈе№ҙиј•дәәпјҢзӮәи‘—дҪ еҖ‘еңӢ家民主зҡ„жңӘдҫҶд»ҳеҮәдҪ еҖ‘зҡ„з”ҹе‘ҪпјҢе°ұеҰӮеҗҢе®үе©·еӢҮж•ўгҖҒзҙ°иҶ©зҡ„жӯЈеңЁеҒҡзҡ„гҖӮBravo!в”Җв”ҖеҸІеқҰеҲ©пјҺеҚЎиҢІпјҲStanley N. KatzпјүпјҢжҷ®жһ—ж–Ҝй “еЁҒзҲҫйҒңеңӢйҡӣиҲҮе…¬е…ұдәӢеӢҷеӯёйҷўж•ҷжҺҲ
гҖҖгҖҖдҪ жңүеӨҡд№…жІ’еҘҪеҘҪж“ҒжҠұиҮӘе·ұпјҢе’ҢиҮӘе·ұеҘҪеҘҪиӘӘиӘӘи©ұдәҶпјҹдҪ жӣҫйҒҮиҰӢзңҹеҜҰзҡ„иҮӘе·ұе—ҺпјҹдҪ иҰҒжҖҺжЁЈиЎЎйҮҸдҪ зҡ„дәәз”ҹпјҹжүҖи¬ӮжҲҗеҠҹпјҢеҲ°еә•иҰҒжҖҺжЁЈе®ҡзҫ©пјҹдҪ еңЁд№Һзҡ„жҳҜжҲҗе°ұд»ҖйәјдәӢжғ…пјҢйӮ„жҳҜжҲҗзӮәд»ҖйәјжЁЈзҡ„дәәпјҹеҰӮжһңжӯ·з·ҙжҳҜдәәз”ҹзҡ„еҝ…й ҲпјҢеңЁе“ӘиЈЎе°ӢжүҫеӢҮж°Јпјҹз”ЁдҪ•жі•жҢҒе®ҡж–№еҗ‘пјҹеҸҲеҰӮдҪ•еҫ—и‘—еҠӣйҮҸпјҹе®үе©·еӨ§ж–№ж•һй–ӢиҮӘе·ұпјҢеҪ·еҪҝз”ЁдёҖж”Ҝж”Ҝй‘°еҢҷпјҢеұӨеұӨжү“й–ӢдёҖжң¬жң¬ж—ҘиЁҳпјҢйӮЈжҳҜз”Ёе№іеҮЎзҡ„з”ҹе‘ҪпјҢеҚ»еӣ зӮәеҘҪеҘҪжҖқзҙўдәҶдёҠйқўзҡ„е•ҸйЎҢпјҢеӢҮж•ўиёҸеҮәиЎҢеӢ•пјҢи®“е№ҙиј•зҡ„з”ҹе‘ҪеңҚз№һи‘—дёҚе№іеҮЎзҡ„ж•…дәӢгҖӮдҪ зҡ„дәәз”ҹеҠҮжң¬еҸҜиғҪеӨ§дёҚзӣёеҗҢпјҢдҪҶжҲ‘ж·ұдҝЎйӮЈдёҚе№іеҮЎзҡ„ж•…дәӢпјҢдёҖжЁЈиғҪеӨ еңЁдҪ иө°йҒҺзҡ„жҜҸдёҖеҖӢи¶іи·Ўдёӯй–ғй–ғзҷјдә®пјҒжү“й–ӢйҖҷжң¬жӣёеҘҪеғҸи·ідёҠдәҶж·ұе…ҘеҸўжһ—зҡ„и¶ҠйҮҺи»ҠпјҢдёҖи·Ҝй©ҡеҳҶйЎӣз°ёпјҢеҚ»д№ҹдёҚеҫ—дёҚеёёеёёз·ҠжҖҘз…һи»ҠпјҢзҙ°зҙ°е“Ғе‘ійҡұи—ҸеңЁеҸўжһ—дёӯзҡ„жҷәж…§пјҢйқһеёёйҒҺзҷ®гҖӮв”Җв”ҖжқңжҳҺзҝ°пјҢеңӢйҡӣдё–з•Ңеұ•жңӣжңғдәһжҙІеёӮе ҙиІ иІ¬дәәгҖҒеүҚеҸ°зҒЈдё–з•Ңеұ•жңӣжңғжңғй•·
гҖҖгҖҖйҒҮиҰӢе®үе©·жҳҜж®өзҫҺйә—зҡ„з·ЈеҲҶгҖӮжҲ‘еҖ‘иғҢжҷҜзӣёдјјпјҡйғҪеңЁзҫҺеңӢи®ҖжӣёгҖҒдё»дҝ®е…¬е…ұиЎҢж”ҝгҖҒе°ҚйқһзҮҹеҲ©жңҚеӢҷж“ҒжңүзҶұеҝұгҖӮдәҢв—ӢдёҖдёүе№ҙйҖҸйҒҺе®үе©·зҲёзҲёиӘҚиӯҳеҘ№жҷӮпјҢйӣ–然еҘ№еңЁзҫҺеңӢгҖҒжҲ‘еңЁеҸ°зҒЈпјҢйҖҸйҒҺ Skype дәӨи«ҮеҚ»жңүзЁ®зҶҹжӮүж„ҹгҖӮе®үе©·еҫҲзңҹиӘ гҖҒзҶұжғ…ең°иҲҮжҲ‘еҲҶдә«Teach For Taiwanзҡ„еӨўжғіпјҢеҘ№зҡ„йЎҳжҷҜиҲҮеҹ·иЎҢеҠӣи®“жҲ‘еҫҲж¬ЈиіһпјҢй–Ӣе•ҹдәҶжҲ‘еҖ‘д№Ӣй–“жӣҙеӨҡдәӨйӣҶпјҡжҲ‘еҖ‘йғҪеёҢжңӣз”ЁеҜҰйҡӣиЎҢеӢ•зӮәзӨҫжңғеё¶дҫҶжӯЈеҗ‘ж”№и®ҠгҖҒйҒёж“ҮеңЁдәҢеҚҒдҫҶжӯІжҷӮеүөжҘӯгҖҒд№ҹеңЁеҗҢдёҖиҫҰе…¬е®ӨдёҖиө·еҘ®й¬ҘгҖӮеҫҲжҰ®е№ёеҸғиҲҮе®үе©·иҚүеүөTFTзҡ„йҒҺзЁӢпјҢдёҖи·ҜзңӢи‘—еҘ№иҫӯжҺүе·ҘдҪңжҗ¬еӣһеҸ°зҒЈгҖҒжүҫе°Ӣ第дёҖжү№еӨҘдјҙгҖҒйҒҮиҰӢ第дёҖдҪҚжҠ•иіҮиҖ…гҖҒжӢӣеӢҹ第дёҖжү№зЁ®еӯҗж•ҷеё«зӯүпјҢеҜҰеңЁз”ұиЎ·дҪ©жңҚпјҢеӣ зӮәдәҢеҚҒдёүжӯІжҷӮзҡ„жҲ‘пјҢжІ’жңүе®үе©·зҡ„жұәеҝғе’ҢжҜ…еҠӣгҖӮзӣёдҝЎжң¬жӣёжңғи®“еӨ§е®¶жӣҙиӘҚиӯҳйҖҷдҪҚеӢҮж•ўжҠ•иә«еҸ°зҒЈж•ҷиӮІгҖҒдәәзҫҺеҝғд№ҹзҫҺзҡ„еӨўжғігҖҢеҝ—гҖҚйҖ 家пјҒв”Җв”Җжһ—д»Ҙж¶өпјҢзӨҫдјҒжөҒеүөиҫҰдәә
гҖҖгҖҖеҸ°зҒЈдёҚд№Ҹй«ҳеӯёжӯ·зҡ„еӯ©еӯҗгҖӮдҪҶжңүзҗҶжғігҖҒжңүеӢҮж°ЈгҖҒжңүиҮӘе·ұжғіжі•пјҢйӮ„иғҪе°ҚеҸ°зҒЈеҝөиҢІеңЁиҢІзҡ„еӯ©еӯҗеӨӘе°‘гҖӮе®үе©·жҳҜйҖҷжЁЈзҡ„е„Әз§Җеӯ©еӯҗгҖӮеҫҲйӣЈжғіеғҸпјҢTeach For TaiwanйҖҷжЁЈзҡ„еӨ§иӯ°йЎҢпјҢжңғжҳҜдёҖзҫӨдәҢеҚҒдҫҶжӯІзҡ„еӯ©еӯҗзҫ©з„ЎеҸҚйЎ§ең°жүӣдәҶиө·дҫҶпјҢе®үе©·е’ҢйҖҷзҫӨиҸҒиӢұпјҢж“”и‘—йҮҚйҮҸеҚ»д№ҹйӣ„е§ҝиӢұзҷјпјҢеҖјеҫ—жңҹеҫ…пјҒйҖҷжң¬жӣёпјҢж•ҳиҝ°е®үе©·еңЁжҷ®жһ—ж–Ҝй “еӨ§еӯёжңҹй–“пјҢеҲ°жӯҗгҖҒзҫҺгҖҒдәһгҖҒйқһеӣӣеӨ§жҙІзҡ„и¶іи·ЎиҲҮжҲҗй•·гҖӮд№ҹиЁұеңЁйҖҷеӯ—еӯ—еҸҘеҸҘиЈЎпјҢдҪ е°ҮжүҫеҲ°жҲҗй•·иҲҮиӣ»и®ҠжүҖйңҖиҰҒзҡ„йӨҠеҲҶиҲҮи»Ңи·ЎгҖӮйҖҷжҳҜе®үе©·зҡ„еғ№еҖјпјҢд№ҹжҳҜйҖҷжң¬жӣёзҡ„гҖӮв”Җв”Җв”ҖйҷідҝҠжң—пјҢеӯ©еӯҗзҡ„жӣёеұӢеүөиҫҰдәә
гҖҖгҖҖеҸ°еҢ—еҮәз”ҹпјҢеҸ°дёӯй•·еӨ§зҡ„еҸ°зҒЈеӣқд»”гҖӮ2008е№ҙеҫһеҸ°дёӯеҘідёӯз•ўжҘӯжҷӮпјҢеҗҢжҷӮжҺЁз”„дёҠеҸ°еӨ§еӨ–ж–ҮиҲҮж”ҝжІ»зі»пјҢд№ҹиҮӘеӯёиӢұж–ҮиҖғдёҠзҫҺеңӢеҚҒжүҖеҗҚж ЎпјҢжңҖеҫҢйҒёж“Үе°ұи®ҖжҸҗдҫӣе…ЁйЎҚзҚҺеӯёйҮ‘зҡ„жҷ®жһ—ж–Ҝй “еӨ§еӯёгҖӮ2012е№ҙж–јжҷ®жһ—ж–Ҝй “еӨ§еӯёгҖҢеЁҒзҲҫйҒңе…¬е…ұиҲҮеңӢйҡӣдәӢеӢҷеӯёйҷўгҖҚз•ўжҘӯеҫҢпјҢжӣҫж–јзҙҗзҙ„жҹҗйҶ«зҷӮйЎ§е•Ҹз®ЎзҗҶе…¬еҸёе·ҘдҪңпјҢеҫҢж”ҫжЈ„й«ҳи–ӘпјҢзұҢиҫҰTeach For TaiwanпјҲзӮәеҸ°зҒЈиҖҢж•ҷпјүиЁҲз•«пјҢеӣһеҸ°ең“еӨўгҖӮ
еҘҪи©•жҺЁи–Ұ
иҮӘгҖҖеәҸпјҸиҮҙжҲ‘зҡ„зҲ¶жҜҚгҖҖ
1жөҒжөӘпјҡиө·й»һ
йҖҷдё–дёҠеҸӘжңүе…©зЁ®жөҒжөӘдәәпјҡдёҖзЁ®жҲҗзӮәеҸ—е®іиҖ…пјҢйҒёж“ҮеңЁеЎһзҙҚжІізөӮзөҗз”ҹе‘Ҫпјӣ
еҸҰдёҖзЁ®пјҢжҲҗзӮәжҲ°еЈ«пјҢз”Ёд»–еҖ‘жүҖжңүзҡ„ж„ҒеҺ»е»әзҜүдёҖеҖӢи®“д»–еҖ‘еӨ§еӨ§еұ•зҝ…й«ҳйЈӣзҡ„еј•ж“ҺгҖӮ
2иҝҰзҙҚпјҡеӢҮж•ўеҒҡдёҖж¬ЎзҷҪзҙҷ
жҒӯе–ңеҰіпјҢеңЁзңҫдәәдёӯзҚІйҒёжҲҗзӮәеҚҒдә”дҪҚиЁҲз•«еҸғиҲҮиҖ…д№ӢдёҖгҖӮ
еҰіжҳҜејөзҷҪзҙҷпјҢжӯЎиҝҺдҫҶйқһжҙІпјҢдҫҶжҹ“дёҠжҲ‘еҖ‘зңҹжӯЈзҡ„йЎҸиүІгҖӮ
3жҷ®жһ—ж–Ҝй “пјҲдёҠпјүпјҡеҰіжҳҜжҖҺйәјиҖғдёҠзҡ„пјҹ
йӣ–然ж—ҘиЁҳдёӯеҜ«и‘—гҖҢж–°з”ҹиҲ¬зҡ„й©ҡеҘҮгҖҚпјҢдҪҶ當жҲ‘еҺ»и®Җ當жҷӮзҡ„з¶ІиӘҢпјҢ
еҺҹдҫҶеҒҡж–°з”ҹзҡ„гҖҢй©ҡеҘҮгҖҚпјҢеӨ§жҰӮеҸӘз¶ӯжҢҒдәҶдёҚеҲ°дёҖйҖұзҡ„иңңжңҲжңҹгҖӮ
4е·ҙй»ҺпјҡжөҒеӢ•зҡ„йҘ—е®ҙ
еҰӮжһңдҪ еӨ е№ёйҒӢпјҢеңЁе№ҙиј•жҷӮеҫ…йҒҺе·ҙй»ҺпјҢйӮЈйәј
е·ҙй»Һе°Үж°ёйҒ и·ҹи‘—дҪ пјҢеӣ зӮәе·ҙй»ҺжҳҜдёҖеёӯжөҒеӢ•зҡ„йҘ—е®ҙгҖӮ
5жө·ең°пјҡдёҖз„ЎжүҖжңүдёӯзҡ„еҜҢи¶і
еңЁдәәзңӢдҫҶпјҢжҲ‘еҖ‘жҳҜжңҖиІ§зӘ®зҡ„пјӣ
дҪҶжҲ‘зҹҘйҒ“пјҢеңЁзҘһзңӢдҫҶпјҢжҲ‘еҖ‘жҳҜжңҖеҜҢжңүзҡ„гҖӮ
6ж—Ҙе…§з“ҰпјҡиҲ’йҒ©еңҲдёӯзҡ„дёҚиҲ’йҒ©
е»әиӯ°еҰіпјҢжҢ‘жҲ°иҮӘе·ұжҡ«жҷӮйӣўй–ӢйқһзҮҹеҲ©ж©ҹж§ӢйҖҷеҖӢиҲ’йҒ©еңҲпјҢ
еҰӮжһңжңүеӨ©еӣһеҲ°йҖҷеҖӢй ҳеҹҹпјҢеҰіе°ұеҸҜд»Ҙз«ҷеңЁдёҚдёҖжЁЈзҡ„й«ҳеәҰзңӢйҖҷиЈЎзҡ„е·ҘдҪңгҖӮ
7еңЁзӣЈзҚ„ж•ҷжӣёзҡ„ж—ҘеӯҗпјҡиҖҒеё«пјҢеҰізӮәд»ҖйәјдҫҶпјҹ
еҰӮжһңжҲ‘жІ’жңүиҫҰжі•иӘӘжңҚеӯёз”ҹе’ҢиҮӘе·ұгҖҢжҲ‘зӮәд»ҖйәјдҫҶгҖҚпјҢ
йӮЈйәјеҶҚжЈ’зҡ„зҗҶи«–гҖҒ經驗гҖҒж–№жі•гҖҒе·Ҙе…·пјҢйғҪз„Ўжі•и®“еӯёз”ҹйЎҳж„ҸиҒҪжҲ‘иӘӘи©ұгҖӮ
8жҷ®жһ—ж–Ҝй “пјҲдёӢпјүпјҡз ҙз№ӯиҖҢеҮә
еӣӣе№ҙеүҚпјҢжҲ‘йӮ„жҳҜеҖӢиў«дәә笑гҖҢжҖҺйәјиҖғеҫ—дёҠжҷ®жһ—ж–Ҝй “гҖҚзҡ„з„ЎеҠ©еҘіз”ҹпјӣ
еӣӣе№ҙеҫҢпјҢжҲ‘е®ҢжҲҗдәҶдёҖзҷҫдә”еҚҒй Ғзҡ„и«–ж–ҮпјҢйӮ„еҫ—еҲ°и«–ж–ҮйҰ–зҚҺ……
9зӨҫжңғж–°й®®дәәпјҡж„ҹи¬қзөҰдҪ 第дёҖд»Ҫе·ҘдҪңзҡ„дәә
幫еҰіеҒҡпјҢеҸҜиғҪзңҒе№ҫеҲҶйҗҳпјҢдҪҶеҸӘжҳҜ延йҒІзІҫзҶҹгҖҒжӢ–延жңӘдҫҶжӣҙеӨҡдәәзҡ„жҷӮй–“гҖӮ
еҰіжңҖиғҪ幫жҲ‘еҖ‘зңҒжҲҗжң¬зҡ„ж–№жі•пјҢе°ұжҳҜжӢҡдәҶе‘Ҫзҡ„еӯёпјҒ
10еӣһеҸ°зҒЈзҡ„и·ҜпјҡжҚІиө·иў–еӯҗпјҢжҲҗзӮәж”№и®Ҡзҡ„иө·й»һ
жҲ‘еҖ‘жғіиҰҒж”№и®Ҡзҡ„дәәгҖҒдәӢгҖҒзү©йҖҷйәјеӨҡпјҢжғіиҰҒи§Јжұәзҡ„е•ҸйЎҢйҖҷйәјеӨ§пјҢ
дҪҶпјҢжҲ‘еҖ‘жңҖйңҖиҰҒгҖҒд№ҹжңҖеҸҜд»Ҙж”№и®Ҡзҡ„пјҢжҳҜеұ¬ж–јжҲ‘еҖ‘иҮӘе·ұзҡ„дё–д»ЈгҖӮ
еҫҢиЁҳпјҸй—ңж–јдё–д»ЈгҖҖ
3жҷ®жһ—ж–Ҝй “пјҲдёҠпјүпјҡеҰіжҳҜжҖҺйәјиҖғдёҠзҡ„пјҹ
HeyпјҢжңӘдҫҶзҡ„еҰіпјҢиЁҳеҫ—иҖғдёҠжҷ®жһ—ж–Ҝй “зҡ„жҷӮеҖҷеҰіиӘӘйҒҺпјҢжңӘдҫҶдёҚи«–зҷјз”ҹд»ҖйәјдәӢпјҢдёҚиҰҒеҝҳиЁҳеҰіжңүеӨҡе№ёйҒӢгҖӮеҰіе®іжҖ•зҡ„жҳҜд»ҖйәјпјҹжҳҜеӣӣе№ҙеӨӘзҹӯпјҹжҳҜеҰіжҳҜеҖӢйҢҜиӘӨпјҹжҳҜжүҫдёҚеҲ°гҖҢйӮЈеҖӢд»–гҖҚпјҹжҳҜеҲҘдәәж°ёйҒ жҜ”еҰіе®ҢзҫҺпјҹеҰідёҚйҮҚиҰҒпјҹиҰӘж„ӣзҡ„жңӘдҫҶзҡ„еҰіпјҢжҲ‘зӣёдҝЎз•¶еҰізңӢеҲ°йҖҷе°ҒдҝЎпјҢеҰіжңғеҫ®з¬‘и‘—иӘӘпјҡгҖҢдёҖеҰӮйҒҺеҫҖпјҢзҘһеё¶й ҳжҲ‘и·ЁйҒҺдёҖеҲҮгҖӮгҖҚзҘһе•ҠпјҢжұӮ祢зөҰжҲ‘йЈҪж»ҝзҡ„еҝғпјҢиў«祢е……ж»ҝзҡ„ж„ӣгҖӮжҢӘеҺ»дёҚи¶ізҡ„з©әиҷӣпјҢзҘһе•Ҡ當жҲ‘зҷ»дёҠеұұй ӮпјҢи®“жҲ‘иҲүзӣ®и®ҡзҫҺ祢пјӣ當жҲ‘еңЁеұұи°·пјҢжұӮ祢и®“жҲ‘е®ҡзқӣеңЁ祢зҡ„йҷҪе…үгҖӮ
и®“жҲ‘дёҚиҮӘж»ҝпјҢдёҚеҖҡйқ иҮӘе·ұпјҢдёҚиҰҒеҝҳиЁҳ祢зҡ„еҒүеӨ§гҖӮ
в”Җв”ҖжҲ‘еҜ«зөҰжңӘдҫҶиҮӘе·ұзҡ„дҝЎпјҢ2008/10/26
зҸҫеңЁзҡ„жҲ‘пјҢеҠӘеҠӣжғіиҰҒиЁҳиө·еүӣжҠөйҒ”жҷ®жһ—ж–Ҝй “жҷӮзҡ„зЁ®зЁ®пјҢиЁҳжҶ¶еҘҪеғҸ已經й–Ӣе§ӢдёҚеӨӘй…ҚеҗҲгҖҒз•«йқўе·Із¶“жңүдёҖдәӣжЁЎзіҠгҖӮдҪҶжңүи¶Јзҡ„жҳҜпјҢ當жҲ‘еҳ—и©Ұй–үдёҠзңјзқӣпјҢжғіз”Ёең–еғҸеҺ»йҮҚжә«з•¶ж–°й®®дәәзҡ„йӮЈж®өж—ҘеӯҗпјҢи…Ұжө·дёӯжө®зҸҫзҡ„пјҢжҳҜдёҖе№…е№…зҫҺеҰӮи©©з•«зҡ„жҷҜиұЎпјҡеҫһжңЁй ӯжҗӯзҡ„е°ҸзҒ«и»Ҡз«ҷиө°еҮәдҫҶпјҢд»°жңӣй«ҳиҒіиҺҠеҡҙзҡ„еёғиҗҠзҲҫеЎ”пјҢжҺҘи‘—йӮҠзҲ¬и‘—дёҖйҡҺйҡҺзҡ„жЁ“жўҜпјҢйӮҠзңӢи‘—дёҚйҒ иҷ•зҡ„дәһжӯ·еұұеӨ§зҰ®е ӮпјҢд»ҘеҸҠеҘ№еӨ–зүҶдёҠеҲ»зҡ„жӢүдёҒж–ҮпјҡгҖҢжІ’жңүжҜ”й«ҳиҲүжҷәиҖ…еӯёзҝ’зҡ„еҜ§йқңдҪҸжүҖжӣҙж·ұзҡ„е–ңжӮ…гҖҚгҖӮ
жҲ‘иЁҳеҫ—第дёҖж¬ЎиёҸйҖІжңҖеҸӨиҖҒзҡ„жӢҝж’’жЁ“пјҢиҒҪи‘—иҝҙзӣӘзҡ„и…іжӯҘиҒІпјҢжғіеғҸи‘—е…©зҷҫеӨҡе№ҙеүҚйәҘиҝӘйҒңеңЁйҖҷиЈЎиө°еӢ•гҖӮ
иЁҳеҫ—еӨ§дёҖдҪҸзҡ„еқҺеёғзҲҫжЁ“пјҢзҹій ӯз ҢжҲҗзҡ„жЁ“жўҜ已經被иёҸеҲ°еҮ№йҷ·пјҢиҖҢеӨ§дәҢдҪҸзҡ„дҫҜеҫ·жЁ“пјҢжҲҝиЈЎжңүеҸӨиҖҒзҡ„зҒ«зҲҗпјҢжҲҝеӨ–жҳҜжӢҚж”қгҖҢзҫҺйә—дәәз”ҹгҖҚзҡ„жӢұеһӢй•·е»ҠпјҢйҖҡеҫҖйңҚж јиҸҜиҢІиҲ¬зҡ„дәӨиӘје»ігҖӮ
иЁҳеҫ—жҲ‘жңҖе–ңжӯЎзҡ„жқұжҙҫжҒ©жЁ“пјҢз”Ёзҙ…иүІзЈҡзҹіз ҢжҲҗеҸЈеӯ—пјҢеҫһдёӯеәӯдёӯеӨ®иө°йҖІеҺ»пјҢдҫҝеҸҜд»ҘйҖҡеҲ°еңЁжҲ‘еҝғзӣ®дёӯпјҢе…Ёжҷ®жһ—ж–Ҝй “жңҖзҫҺзҡ„жҲҝй–“пјҡе…ЁйғЁз”ЁжңЁй ӯе»әжҲҗзҡ„е…«еӯ—еһӢең–жӣёе®ӨпјҢжңүи‘—й«ҳжҢ‘зҡ„жңЁйӣ•еӨ©иҠұжқҝпјҢж—Ҙе…үиҮӘ然зҡ„е…ЁеӨ©еҫһеҗ„ж–№зҡ„еҪ©з№ӘзҺ»з’ғе°„е…ҘпјҢжҜҸеҖӢи§’иҗҪйғҪж“әи‘—еӨ©йөқзөЁзҡ„жү¶жүӢжӨ…пјҢйӮ„жңүйҖҡеҫҖдёҖеҖӢеҖӢзӣёйҖҡзҡ„е°Ҹй–ЈжЁ“зҡ„жЁ“жўҜ……
еҶҚз№јзәҢеҜ«пјҢеҸҜиғҪдёҖж•ҙеҖӢз« зҜҖйғҪеҜ«дёҚе®ҢгҖӮйҖҷдёҚеҸӘжҳҜеүӣе…ҘеӯёжҷӮзҡ„ж„ҹиҰәиҖҢе·ІгҖӮз•ўжҘӯеҫҢпјҢдёҖж¬Ўжңүж©ҹжңғеӣһеҲ°еӯёж ЎеҸғеҠ еңҳеҘ‘жҙ»еӢ•еҫҢпјҢеңЁеҜ’йўЁдёӯжғіеҫһеңҳеҘ‘жүҖеңЁзҡ„еўЁйӣ·е°ҸеұӢеҝ«жӯҘиәІеӣһжә«жҡ–зҡ„и»ҠиЈЎгҖӮеҝҪ然пјҢжҲ‘з„Ўж„Ҹзҡ„жҠ¬й ӯдёҖзңӢпјҢе°ұдёҚз”ұиҮӘдё»зҡ„еҒңдёӢи…іжӯҘпјҢиў«йҖҷдёҚ經ж„Ҹзҡ„зҫҺгҖҒй…ҚдёҠж»ҝеӨ©жҳҹжҳҹе’Ң全然еҜӮйқңзҡ„ж Ўең’пјҢе®Ңе…ЁйңҮжҮҫдҪҸдәҶгҖӮ
йӮЈеӨ©пјҢжҲ‘еңЁж—ҘиЁҳдёҠеҜ«дёӢйҖҷж®өи©ұпјҡ
“I just want myself to remember something. I was walking from Murray Dodge to my car, this walk that couldn’t have been more familiar, yet I hadn’t done in such a long time. I remembered that awe, that joy of taking ownership of this amazing place. I want myself to remember that gratitude for calling this place home.”
жҲ‘еҸӘжғіиҰҒжҲ‘иҮӘе·ұиЁҳеҫ—йҖҷеҖӢпјҡжҲ‘еүӣеүӣеҫһеўЁйӣ·е°ҸеұӢиө°еҗ‘жҲ‘зҡ„и»ҠпјҢйҖҷжҳҜдёҖжўқжҲ‘еҶҚзҶҹжӮүд№ҹдёҚйҒҺзҡ„и·Ҝеҫ‘пјҢеҸӘдёҚйҒҺз•ўжҘӯеҫҢжҲ‘еҫҲд№…жІ’жңүиө°дәҶгҖӮдҪҶжҲ‘дҫқ然иЁҳеҫ—йӮЈж–°з”ҹиҲ¬зҡ„й©ҡеҘҮпјҢйӮЈеҸҜд»ҘжҲҗзӮәйҖҷең°ж–№жүҖжңүдәәд№ӢдёҖзҡ„е–ңжӮ…гҖӮжҲ‘жғіиҰҒжҲ‘иҮӘе·ұиЁҳеҫ—йҖҷд»Ҫж„ҹжҒ©пјҢйҖҷд»ҪеҸҜд»ҘеҸ«йҖҷең°ж–№гҖҢ家гҖҚзҡ„ж„ҹжҒ©гҖӮ
зҹӯжҡ«зҡ„ж–°з”ҹиңңжңҲжңҹ
дҪҶжңүи¶Јзҡ„жҳҜпјҢйӣ–然ж—ҘиЁҳдёӯжҲ‘еҜ«и‘—гҖҢж–°з”ҹиҲ¬зҡ„й©ҡеҘҮгҖҚпјҢ當жҲ‘е°ҮйҖҷдәӣең–еғҸеҫһи…Ұдёӯжҡ«жҷӮжҠҪйӣўпјҢиҖҢж”№еҺ»и®ҖжҲ‘當жҷӮзҡ„з¶ІиӘҢпјҢеҳ—и©ҰеҺ»иЁҳиө·з•¶жҷӮзҡ„еҝғжғ…пјҢеҒҡж–°з”ҹзҡ„жҲ‘зҡ„гҖҢй©ҡеҘҮгҖҚпјҢеӨ§жҰӮеҸӘз¶ӯжҢҒдәҶдёҚеҲ°дёҖйҖұзҡ„иңңжңҲжңҹгҖӮ
第дёҖеҖӢеӣ°йӣЈпјҢеҫһдәӨжңӢеҸӢй–Ӣе§ӢгҖӮйӣ–然еҫһдёҖй–Ӣе§ӢжҲ‘е°ұеӣ зӮәеҸғеҠ зӨҫеңҳиҲҮеңҳеҘ‘иҖҢиӘҚиӯҳдёҚе°‘жңӢеҸӢпјҢдҪҶжҳҜе°ҸеҫһиӢұж–Үи«әиӘһгҖҒ笑и©ұзҡ„иҒҪдёҚжҮӮпјҢеӨ§иҮіе®Ңе…ЁжңғйҢҜж„ҸгҖҒиә«й«”з•Ңз·ҡеҠғеҲҶдёҚеҗҢпјҢи®“жҲ‘жҷӮеёёжҲҗзӮәеҗҢеӯёеҖ‘йӣ–з„ЎжғЎж„ҸпјҢдҪҶз„Ўжі•е…ӢеҲ¶зҡ„еҳІз¬‘е°ҚиұЎгҖӮ
жҜ”ж–№иӘӘпјҢйӮЈжҷӮжҲ‘д»ҘзӮәгҖҢdufflebagгҖҚиҲҮгҖҢdouchebagгҖҚжҳҜеҗҢзҫ©еӯ—пјҢдҪҶдәӢеҜҰдёҠеүҚиҖ…жҳҜгҖҢиЎҢжқҺиўӢгҖҚзҡ„ж„ҸжҖқпјҢеҫҢиҖ…еҺҹж„ҸжҳҜгҖҢеҘіжҖ§з§ҒеҜҶиҷ•зҒҢжҙ—иўӢгҖҚпјҢеҫҢдҫҶиў«жӢҝдҫҶеҒҡзӮәзҪөдәәд№Ӣз”ЁпјҢ當然жңүжҡ—е–»иў«зҪөиҖ…жұҷз©ўдёҚе ӘгҖҒзӮәиҮӘеӨ§зӢӮеҰ„д№Ӣеҫ’пјҢжҲ–з”ЁзҸҫд»ЈдёҖй»һзҡ„иӘӘжі•пјҢйЎһдјјгҖҢж©ҹи»ҠзҺӢгҖҚгҖҒгҖҢи¶…зҷҪзҲӣгҖҚзҡ„ж„ҸжҖқгҖӮдҪҶеӨ©зңҹеҰӮжҲ‘пјҢд»ҘзӮәе…©еҖӢеӯ—йғҪжҳҜиЎҢжқҺиўӢзҡ„ж„ҸжҖқпјҢжүҖд»ҘпјҢеңЁдёҖж¬Ўеӯёз”ҹеңҳй«”еҮәйҒҠиӘӘжҳҺжңғдёҠпјҢ當被е•ҸеҲ°жҲ‘жңғж”ңеё¶е№ҫ件иЎҢжқҺпјҢжҲ‘еӣһзӯ”пјҡгҖҢе–”пјҢе°ұжҳҜе…©еҖӢ douchebagsгҖӮгҖҚдё»жҢҒдәәж„Ј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е•ҸпјҡгҖҢе‘ғпјҢи«Ӣе•ҸеҰізҡ„ж„ҸжҖқжҳҜ……е…©еҖӢеҫҲиЁҺеҺӯзҡ„дәәпјҢйӮ„жҳҜе…©еҖӢжё…жҙ—иўӢ……пјҹгҖҚжҺҘи‘—пјҢе…Ёе ҙеҗҢеӯёе“„е ӮеӨ§з¬‘пјҢиҖҢжҲ‘пјҢеүҮжҳҜжҒЁдёҚеҫ—жңүеҖӢең°жҙһеҸҜд»Ҙй‘ҪйҖІеҺ»гҖӮ
еҸҰдёҖеҖӢдҫӢеӯҗпјҢжҳҜжҲ‘е°ҮгҖҢget laid offгҖҚе’ҢгҖҢget laidгҖҚе…©еҖӢзүҮиӘһжҗһж··дәҶпјҡеүҚиҖ…жҳҜгҖҢиў«иЈҒе“ЎгҖҚзҡ„ж„ҸжҖқпјҢеҫҢиҖ…еүҮжҳҜйқһеёёзІ—дҝ—зҡ„иӘӘгҖҢиў«дёҠеәҠгҖҚзҡ„ж„ҸжҖқгҖӮжңүдёҖеӨ©пјҢжҲ‘жҺҘеҲ°йҳҝе§Ёзҡ„йӣ»и©ұпјҢе‘ҠиЁҙжҲ‘е§ЁдёҲдёҚе№ёиў«иЈҒе“ЎдәҶгҖӮжҺӣдёҠйӣ»и©ұпјҢжҲ‘еӮ·еҝғзҡ„иө°еӣһжҲҝй–“пјҢйӮЈиЈЎжңүдёҖеӨ§зҫӨжңӢеҸӢиҒҡеңЁдёҖиө·зңӢйӣ»иҰ–иҒҠеӨ©гҖӮжҲ‘з…һжңүд»ӢдәӢзҡ„жӢҝиө·йҒҷжҺ§еҷЁпјҢй—ңдёҠйӣ»иҰ–пјҢеӨ§иҒІиӘӘпјҡгҖҢеӨ§е®¶пјҢжҲ‘жңүеҖӢеҫҲд»ӨдәәеӮ·еҝғзҡ„ж¶ҲжҒҜпјҡMy uncle just got laid.гҖҚеҗҢеӯёеҖ‘е…ЁйғЁйңІеҮәй©ҡжҒҗз„ЎжҜ”зҡ„иЎЁжғ…пјҢжҲ‘еҝғдёӯй»ҳй»ҳзҡ„й©ҡиЁқеӨ§е®¶з«ҹеҰӮжӯӨеңЁд№ҺжҲ‘е§ЁдёҲпјҢеҘҪз”ҹж„ҹеӢ•гҖӮжңүеҖӢеҗҢеӯёе•ҸпјҡгҖҢеҰі……зӮәд»Җйәјжңғе’ҢеҰіе§ЁдёҲиҒҠйҖҷеҖӢпјҹгҖҚжҲ‘ж„ҹеҲ°иҺ«еҗҚе…¶еҰҷпјҢеӣһзӯ”пјҡгҖҢйҖҷжңүд»ҖйәјдёҚиғҪиҒҠзҡ„пјҹгҖҚеӨ§е®¶йқўйқўзӣёиҰ·пјҢзөӮж–јжңүеҖӢжңӢеҸӢиӘӘпјҡгҖҢе®үе©·пјҢжҲ‘зҢңпјҢеҰіеүӣеүӣжғіиӘӘзҡ„пјҢжҳҜ getting laid offпјҢдёҚжҳҜ getting laid...гҖҚйЎҜ然зҡ„пјҢеӨ§еӨҘеҸҲжҳҜдёҖйҷЈе“„е ӮеӨ§з¬‘пјҢ笑еҲ°зңјж·ҡйғҪжөҒеҮәдҫҶдәҶгҖӮй ҶдҫҝдёҖжҸҗпјҢдёҠиҝ°е…©еҖӢдҫӢеӯҗеҜҰеңЁеӨӘеҸ—жӯЎиҝҺпјҢжҜҸе№ҙйғҪжңғз”ұеӯёй•·е§ҠзҶұеҝғзҡ„еңЁй–ӢеӯёжҷӮеӮіжүҝзөҰж–°з”ҹзҹҘйҒ“пјҢеҸӘдёҚйҒҺеёҢжңӣзҸҫеңЁж•…дәӢдё»и§’жҳҜиӘ°е·Із¶“иў«еҝҳиЁҳдәҶе°ұжҳҜгҖӮ
гҖҢеҰіеҲ°еә•жҖҺйәјиҖғдёҠжҷ®жһ—ж–Ҝй “зҡ„пјҹгҖҚ
第дәҢеұӨеӣ°йӣЈпјҢдҫҶиҮӘиӘІжҘӯгҖӮжҲ‘йӮ„иЁҳеҫ—пјҢ當жҲ‘еқҗеңЁз¬¬дёҖе ӮгҖҢеҖӢ體經жҝҹеӯёгҖҚзҡ„ж•ҷе®ӨдёӯпјҢеҸ°дёҠзҡ„ж•ҷжҺҲжҳҜдё–з•ҢзҹҘеҗҚзҡ„еӯёиҖ…пјҢжӣҙжҳҜзҫҺеңӢзёҪзөұзҡ„йЎ§е•ҸгҖӮ當他еҸЈжІ«ж©«йЈӣзҡ„и¬ӣи‘—пјҢжҲ‘иә«ж—Ғзҡ„еҗҢеӯёйғҪй»һй ӯеҰӮжҗ—и’ңпјҢжӢҡдәҶе‘Ҫзҡ„жҠ„зӯҶиЁҳпјӣиҖҢжҲ‘пјҢйӣ–然ж•ҷжҺҲзҡ„жҜҸеҖӢеӯ—жӢҶи§ЈеҮәдҫҶжҲ‘йғҪиӘҚиӯҳпјҢдҪҶзө„еҗҲеңЁдёҖиө·пјҢеҚ»и®“жҲ‘еҰӮеҗҢйҙЁеңЁиҒҪйӣ·гҖӮжӣҙд»ӨжҲ‘з·Ҡејөзҡ„пјҢжҳҜжҲ‘дјјд№ҺжҳҜж•ҙй–“ж•ҷе®Өе”ҜдёҖдёҖеҖӢиҒҪдёҚжҮӮзҡ„гҖӮеҫһе°ҸеҲ°еӨ§пјҢжҲ‘еҫһдҫҶжІ’жңүжғіеғҸйҒҺжңүдёҖеӨ©жҲ‘жңғжҲҗзӮәе…ЁзҸӯжңҖз¬Ёзҡ„еӯёз”ҹгҖӮ當дёӢзҡ„жҲ‘пјҢеҘҪж…ҢгҖҒеҘҪжҖ•пјҢеҚ»еҸҲдёҚж•ўи®“д»»дҪ•дәәзҷјзҸҫпјҢеҸӘеҫ—еӣһе®ҝиҲҚиҮӘе·ұжҠұи‘—жӣёиӢҰи®ҖгҖҒи¶Ғе®ӨеҸӢдёҚеңЁзҡ„жҷӮеҖҷпјҢеҶҚеҒ·еҒ·жҺүзңјж·ҡгҖӮ
иҖҢеӨ§дёҖжңҖд»ӨжҲ‘й ӯз—ӣзҡ„дёҖй–ҖиӘІпјҢеҸ«еҒҡгҖҢиӢұж–ҮеҜ«дҪңиӘІгҖҚгҖӮйҖҷжҳҜй–Җе…Ёж ЎеӨ§дёҖз”ҹеҝ…дҝ®зҡ„иӘІзЁӢпјҢдёҚи«–еӯёз”ҹжҳҜеҗҰд»ҘиӢұж–ҮзӮәжҜҚиӘһпјҢеӯёж ЎиҰҒжұӮжҜҸеҖӢеӯёз”ҹеңЁй‘Ҫз ”жӣҙж·ұеҘ§зҡ„зҹҘиӯҳд№ӢеүҚпјҢеҝ…й Ҳе…ҲжңүеӯёиҖ…зЁӢеәҰзҡ„еҹәжң¬еҜ«дҪңиғҪеҠӣгҖӮеӣһй ӯзңӢпјҢжҲ‘еҫҲж„ҹжҝҖйҖҷжЁЈзҡ„иҰҒжұӮпјҢи®“жҲ‘зҡ„иӢұж–ҮеҜ«дҪңпјҢеҫһдёҖеҖӢеҸ°зҒЈй«ҳдёӯз”ҹзҡ„зЁӢеәҰпјҢеңЁеӨ§еӯёеӣӣе№ҙе…§еҝ«йҖҹйҒ”еҲ°зҫҺеңӢ當ең°еӨ§еӯёз”ҹзЁӢеәҰд№ӢдёҠгҖӮдҪҶеӨ§дёҖ當дёӢпјҢйҖҷй–ҖиӘІзңҹзҡ„и®“жҲ‘иӢҰдёҚе ӘиЁҖгҖӮжңҖдё»иҰҒзҡ„еҺҹеӣ жҳҜж•ҷжҺҲзҡ„зү№ж®ҠжҺҲиӘІж–№ејҸпјҡжҜҸеҖӢзҰ®жӢңдёҠиӘІеүҚпјҢжҜҸдҪҚеҗҢеӯёйғҪеҝ…й ҲеҜ«д»Ҫдә”й Ғзҡ„зҹӯж–Үе ұе‘ҠпјҢдёҰдё”еҢҝеҗҚеӮізөҰе…ЁзҸӯеҗҢеӯёпјҢиҖҢжҜҸдҪҚеҗҢеӯёд№ҹеҝ…й ҲеңЁдёҠиӘІеүҚе°Үе…ЁзҸӯзҡ„ж–Үз« зңӢе®ҢгҖӮдёҠиӘІжҷӮпјҢж•ҷжҺҲдҫҝеё¶й ҳи‘—еӨ§е®¶дёҖзҜҮгҖҒдёҖзҜҮдҫҶи©•й‘‘пјҢйј“еӢөеӨ§е®¶иҮӘе·ұеҲҶжһҗжҜҸзҜҮж–Үз« е“ӘиЈЎеҘҪгҖҒе“ӘиЈЎдёҚеҘҪгҖҒзӮәд»Җйәјпјҹ
йҖҷзЁ®еҲәжҝҖзҚЁз«ӢжҖқиҖғпјҢиҖҢдё”е°Үдё»е°Һж¬ҠйӮ„зөҰеӯёз”ҹзҡ„еӯёзҝ’ж–№ејҸпјҢе°Өе…¶жҳҜеңЁжҲ‘иҮӘе·ұжҠ•е…Ҙж•ҷиӮІз•Ңд»ҘеҫҢпјҢзҹҘйҒ“е…¶еҜҰзӣёз•¶зҡ„йӣЈеҫ—пјҢжҳҜеӯёз”ҹзҡ„зҰҸж°ЈгҖӮдә”й Ғе ұе‘Ҡе°ҚжҲ‘зҡ„зҫҺеңӢеҗҢеӯёиҖҢиЁҖжҳ“еҰӮеҸҚжҺҢпјҢдёҠиӘІеүҚдёҖеӨ©жҷҡдёҠдёҚз”Ёе№ҫе°ҸжҷӮдҫҝеҸҜд»ҘеҜ«еҮәдҫҶпјҢдҪҶе°Қ當жҷӮзҡ„жҲ‘иҖҢиЁҖеҚ»з„ЎжҜ”еӣ°йӣЈгҖӮжҲ‘еҝ…й ҲдёҖж•ҙеҖӢзҰ®жӢңдёҚж–·зҡ„зҷјжғігҖҒиө·иҚүгҖҒдҝ®зЁҝпјҢз”ҡиҮійӮ„еҫ—зҶ¬еӨңпјҢжүҚиғҪеҜ«еҮәдёҖд»ҪдёҚжңғеӨӘдёҹиҮүзҡ„е ұе‘ҠгҖӮ
дҪҶжҳҜпјҢжҜҸ當дҫҶеҲ°иӘІе ӮиЈЎпјҢж–Үз« зёҪжҳҜиў«еҗҢеӯёеҖ‘жҜ«дёҚз•ҷжғ…зҡ„жү№и©•пјҡгҖҢйҖҷеҖӢй–Ӣй ӯпјҢе®Ңе…ЁжІ’жңүеҲҮдёӯдё»йЎҢпјҒгҖҚгҖҢйҖҷеҖӢиӯ¬е–»пјҢд№ҹеӨӘйӣўйЎҢдәҶпјҹгҖҚгҖҢйҖҷеҖӢдҫӢеӯҗпјҢжёІжҹ“еҫ—еӨӘйӣўиӯңдәҶпјҒгҖҚгҖҢдҪңиҖ…зҡ„ж–Үжі•йЎҜ然йңҖиҰҒеҠ еј·пјҒгҖҚгҖҢйҖҷеҖӢзөҗе°ҫпјҢдёҖй»һеҠӣйҒ“йғҪжІ’жңүгҖӮгҖҚ……жңҖеҫҢпјҢз”ҡиҮіжңүеҖӢеҗҢеӯёиӘӘпјҡгҖҢйҖҷеҖӢдҪңиҖ…еҲ°еә•жҖҺйәјиҖғдёҠжҷ®жһ—ж–Ҝй “зҡ„е•ҠпјҹгҖҚ
гҖҢеҰіеҲ°еә•жҖҺйәјиҖғдёҠжҷ®жһ—ж–Ҝй “зҡ„е•ҠпјҹгҖҚеӨ©е•ҠпјҢйҖҷеҸҘи©ұе°Қ當жҷӮзҡ„жҲ‘иҖҢиЁҖпјҢж„ҹеҸ—еҸӘиғҪз”ЁдёүеҖӢеӯ—еҪўе®№пјҡгҖҢжӨҺгҖҒеҝғгҖҒз—ӣгҖҚгҖӮжҲ‘еңЁеҝғдёӯеҫҲжғіе°Қд»–еҗ¶е–ҠпјҡгҖҢдҪ зҹҘйҒ“жҲ‘еңЁеҸ°зҒЈдёҠйҒҺе ұзҙҷй ӯжўқе—ҺпјҹдҪ иҰҒжҳҜз”Ёдёӯж–ҮеҜ«дҪ жңғжҜ”ијғеҺІе®іе—ҺпјҹдҪ зҹҘйҒ“жҲ‘жҳҜеӨҡйәјжҜ”дҪ еҠӘеҠӣжүҚиғҪиҖғйҖІдҫҶе—ҺпјҹгҖҚдҪҶзөӮ究пјҢжҲ‘ж„ҸиӯҳеҲ°жҲ‘з”ҹж°Јзҡ„е°ҚиұЎдёҚжҳҜд»–пјҢжҳҜе°Қж–јжң¬иә«зҡ„дҝЎеҝғе’Ңеғ№еҖјйғҪй–Ӣе§ӢеӢ•жҗ–зҡ„иҮӘе·ұгҖӮ
жҺЁи–ҰеәҸдёҖ
дёҚе№іеҮЎзҡ„еӣһ家д№Ӣж—…
зҷҪеҙҮдә®пјҢеҸ°зҒЈеҘ§зҫҺйӣҶеңҳи‘ЈдәӢй•·
еҲқж¬Ўзөҗиӯҳе®үе©·жҳҜеңЁдёҖеҖӢз•ҘзӮәеҒ¶з„¶зҡ„ж©ҹжңғиЈЎпјҢдҪҶеҫһ第дёҖж¬ЎиҰӢйқўпјҢжҲ‘е°ұзҹҘйҒ“еҘ№жңғжҳҜеҖӢдёҚе№іеҮЎзҡ„еӯ©еӯҗгҖӮ
е®үе©·зҡ„дёҚе№іеҮЎпјҢдёҰдёҚеңЁж–јеҘ№з”іи«ӢйҖІе…ҘзҫҺеңӢеҗҚж Ўе°ұи®ҖпјҢжҲ–жҳҜеӨ§еӯёйӮ„жІ’жңүз•ўжҘӯе°ұеҮәзүҲдәҶиҮӘе·ұзҡ„第дёҖжң¬жӣёгҖӮжҲ‘жүҖиӘҚиӯҳзҡ„е®үе©·пјҢеҝғдёӯе§ӢзөӮж“ҒжңүдёҖжҠҠзҚЁзү№зҡ„е°әпјҢеҘ№з”ЁйҖҷжҠҠе°әдҫҶиЎЎйҮҸе‘ЁйҒӯдёҖеҲҮдәәгҖҒдәӢгҖҒзү©зҡ„зөӮжҘөеғ№еҖјпјҢеҘ№жҳҜеҖӢж“Ғжңүжё…жҷ°еғ№еҖјдҝЎеҝөзҡ„еӯ©еӯҗгҖӮ
еҫһеӨ–иЎЁдёҠзңӢпјҢиЁұеӨҡдәәжңғзЁұзҫЁеҘ№еңЁжҷ®жһ—ж–Ҝй “еӨ§еӯёеӢҮж–јжҲҗй•·зҡ„еӢ•дәәж•…дәӢгҖӮиӘІе Ӯд№ӢеӨ–пјҢеҘ№зҡ„и¶іи·ЎйӮ„иёҸйҒҚжӯҗгҖҒзҫҺгҖҒдәһгҖҒйқһеӣӣеӨ§жҙІеӨҡеҖӢеңӢ家пјҢжӣҫеңЁе№ҫе…§дәһзҒЈе’ҢиҝҰзҙҚзҡ„еӯ©еӯҗжҲІж°ҙгҖҒеңЁеЎһзҙҚжІіз•”е’Ңжі•еңӢеҗҢеӯёиҫҜи«–е“ІеӯёгҖҒеңЁеҠ еӢ’жҜ”жө·иҲҮжө·ең°зҡ„зҒҪж°‘дёҖеҗҢйҮҚе»ә家ең’гҖҒеңЁж—Ҙе…§з“Ұж№–з•”е’ҢиҒҜеҗҲеңӢе®ҳе“Ўи«ҮеҲӨгҖҒеңЁж№„е…¬жІіж—ҒиЁӘе•Ҹжҹ¬еҹ”еҜЁеңӢеӢҷеҚҝгҖӮеҘ№д№ҹжӣҫеӣ иӘІжҘӯиҗҪеҫҢеӨӘеӨҡиҖҢиў«ж•ҷжҺҲзҫһиҫұгҖҒжӣҫзӮәдәҶиһҚе…Ҙй…·зӮ«зҡ„жңӢеҸӢзҫӨиҖҢиҝ·еӨұиҮӘе·ұгҖҒд№ҹеңЁз•ўжҘӯжҷӮеӣ и«–ж–Үеҫ—еҲ°йҰ–зҚҺе–ңжҘөиҖҢжіЈгҖӮ
然иҖҢпјҢдәәеҖ‘зңӢдёҚеҲ°зҡ„жҳҜпјҢеңЁеҘ№еҝғдёӯйӮ„жңүдёҖеҖӢжІүйқңзҡ„ең°ж–№гҖӮжҜҸ當еҘ№жңүжүҖз–‘жғ‘пјҢйқўиҮЁиҖғй©—пјҢжҲ–йңҖиҰҒдҪңеҮәй—ңйҚөжұәе®ҡзҡ„жҷӮеҲ»пјҢеҘ№зёҪжңғеӣһеҲ°йӮЈеҖӢең°ж–№пјҢеңЁйӮЈиЈЎжҖқиҖғгҖҒжІүжҫұгҖҒзҘҲзҰұпјӣ然еҫҢпјҢйӮЈжҠҠиЎЎйҮҸдәәеҖ‘зөӮжҘөеғ№еҖјзҡ„е°әпјҢзёҪжңғеңЁжңҖеҫҢеҮәзҸҫпјҢ幫еҠ©йҖҷдҪҚеӨ©зҲ¶жүҖж„ӣзҡ„еӯ©еӯҗеҒҡеҮәжңҖзөӮзҡ„жҠүж“ҮгҖӮе®үе©·дёҚжҳҜдёҖеҖӢиј•ж„ҸеҒҡеҮәжұәе®ҡзҡ„еӯ©еӯҗпјҢеҘ№еңЁж„ҸеҘ№жүҖеҒҡзҡ„жҜҸ件дәӢиғҢеҫҢзҡ„еӢ•ж©ҹгҖҒж„Ҹзҫ©е’Ңзӣ®зҡ„гҖӮ
е°ұйҖҷеҖӢдё–з•ҢиҖҢиЁҖпјҢе®үе©·жҳҜиЎЁзҸҫжҘөзӮәеҚ“и¶Ҡзҡ„еӯ©еӯҗгҖӮеҘ№зҡ„дёҚе№іеҮЎд№Ӣиҷ•пјҢе°ұеңЁж–јеҘ№жІ’жңүд»ҘеҚ“и¶ҠеҒҡзӮәжҸӣеҸ–дё–дҝ—жүҖи¬ӮгҖҢжҲҗеҠҹгҖҚзҡ„еўҠи…ізҹігҖӮзӣёеҸҚең°пјҢеҘ№зңјдёӯжүҖзңӢеҲ°зҡ„пјҢжӣҙеӨҡжҳҜдәәеҖ‘зҡ„зңҹеҜҰйңҖиҰҒпјҢзү№еҲҘжҳҜйӮЈдәӣиІ§зӘ®зҡ„гҖҒдёҚи¶ізҡ„гҖҒиў«еҝҪиҰ–зҡ„пјҢе’ҢйңҖиҰҒй—ңж„ӣзҡ„еӯ©еӯҗеҖ‘гҖӮд»ҘеҘ№йҖҷжЁЈе№ҙиј•зҡ„з”ҹе‘ҪпјҢз«ҹ然已жҳҜеҖӢжҮӮеҫ—гҖҢж„ӣпјҢе°ұжҳҜеңЁеҲҘдәәзҡ„йңҖиҰҒдёҠзңӢиҰӢиҮӘе·ұзҡ„иІ¬д»»гҖҚзҡ„еҜҰиёҗиҖ…гҖӮжҲ‘дёҚеҫ—дёҚе°Қе®үе©·еӨҡй»һеҒҸж„ӣпјҒ
жҲ‘зү№еҲҘе–ңжӯЎйҖҷжң¬ж–°жӣёзҡ„жӣёеҗҚгҖҠеҮәиө°пјҢжҳҜзӮәдәҶеӣһ家гҖӢгҖӮе®үе©·зҡ„зўәиө°йҒҺдёҖжўқжҷ®жһ—ж–Ҝй “жҲҗй•·д№Ӣи·ҜпјҢ然иҖҢ當жҲ‘еҫ—зҹҘеҘ№зөӮж–јжұәе®ҡеӣһеҲ°еҸ°зҒЈпјҢиҰҒеё¶еӢ•е’ҢеҘ№е№ҙйҪЎзӣёд»ҝзҡ„е№ҙиј•дәәеңЁеҸ°зҒЈзҡ„еңҹең°дёҠпјҢйҖІеҲ°еҒҸйҒ ең°еҚҖеҺ»Teach For TaiwanжҷӮпјҢеҪ·еҪҝеҸҲеӣһеҲ°дәҶеҲқж¬ЎиҰӢеҲ°е®үе©·жҷӮиҰәеҫ—еҘ№дёҚе№іеҮЎзҡ„ж„ҹеҸ—пјҢеҸӘжҳҜйҖҷеӣһжӣҙеӨҡдәҶе№ҫеҲҶе°ҚеҘ№жүҖд»ЈиЎЁзҡ„еҸ°зҒЈе№ҙиј•дё–д»Јзҡ„жңҹиЁұиҲҮзҘқзҰҸгҖӮ
жҜҸдёҖеЎҠеңҹең°дёҠзҡ„з№ҒжҰ®пјҢйғҪйңҖиҰҒ經з”ұдё–д»ЈеӮіжүҝдҫҶдёҚж–·еүөйҖ зҷјеұ•гҖӮжҲ‘дёҚйЎҳж„ҸзөҰе®үе©·еӨӘеӨ§зҡ„еЈ“еҠӣпјҢдҪҶжҲ‘иҰҒиӘӘпјҡжҜҸ當зңӢиҰӢеҘ№е…үйҮҮзҮҰзҲӣзҡ„笑容пјҢе°ұжңғиҰәеҫ—еҸ°зҒЈзҡ„дёӢдёҖд»Јд»Қ然жҳҜе……ж»ҝеёҢжңӣзҡ„гҖӮ
е®үе©·иҲҮеӨҘдјҙеҖ‘пјҢдҪ еҖ‘еҠ жІ№пјҒ
жҺЁи–ҰеәҸдәҢ
All you need is some courage!!
и‘үдёҷжҲҗпјҢеҸ°еӨ§йӣ»ж©ҹзі»еүҜж•ҷжҺҲгҖҒеҸ°еӨ§MOOCеҹ·иЎҢй•·гҖҒеҸ°еӨ§ж•ҷеӯёзҷјеұ•дёӯеҝғеүҜдё»д»»
иӘҚиӯҳе®үе©·пјҢжҳҜеҫһжҲ‘еҖ‘еҗҢеҸ°еңЁдәҢв—ӢдёҖдёүе№ҙзҡ„TEDxTaipeiе№ҙжңғжј”и¬ӣй–Ӣе§ӢгҖӮ當жҷӮпјҢжҲ‘еҸӘзҹҘйҒ“еҘ№жҳҜеҖӢеҫһзҫҺеңӢеҗҚж Ўжҷ®жһ—ж–Ҝй “з•ўжҘӯпјҢиҫӯжҺүдәҶдәәдәәзЁұзҫЁзҡ„е·ҘдҪңпјҢеӣһеҸ°еүөз«ӢTeach For TaiwanпјҢз«Ӣеҝ—зӮәеҒҸй„үеӯ©з«Ҙж”№е–„ж•ҷиӮІзҡ„дә®йә—еҘіеӯ©гҖӮеҲқиӯҳжҷӮпјҢжҲ‘и·ҹиЁұеӨҡдәәдёҖжЁЈпјҢеҝғдёӯжңүдёҚе°‘з–‘е•Ҹпјҡ究з«ҹжҳҜд»ҖйәјжЁЈзҡ„еҺҹеӣ пјҢжңғи®“йҖҷеҖӢеҘіеӯ©ж”ҫжЈ„дәҶдё–дҝ—зңје…үдёӯзҡ„дәәз”ҹеқҰйҖ”пјҢйҒёж“ҮдәҶдёҖжўқе……ж»ҝжҢ‘жҲ°гҖҒеёғж»ҝиҚҠжЈҳзҡ„йҒ“и·Ҝпјҹ
дҪҶйҡЁи‘—е°Қе®үе©·зҡ„жӣҙеҠ иӘҚиӯҳпјҢжҲ‘е®Ңе…ЁеҸҜд»ҘзҗҶи§ЈзӮәд»ҖйәјдәҶгҖӮе…¶еҜҰпјҢе®үе©·зҡ„дәәз”ҹ經жӯ·пјҢжӯЈжҳҜжҲ‘еҖ‘當д»ҠеҸ°зҒЈйқ’е№ҙжүҖжңҖж¬ зјәзҡ„дёҖеЎҠпјҡе°ҚиҮӘжҲ‘зҡ„жҺўзҙўиҲҮиӘҚиӯҳгҖӮ
еҸ°зҒЈеӯёеӯҗпјҢеңЁзҲ¶жҜҚзҡ„е‘өиӯ·дёӢпјҢеҫҖеҫҖйғҪд»ҘеӯёжҘӯзӮәйҮҚгҖӮеңЁеӯёжҘӯзҡ„еЈ“еҠӣдёӢпјҢеҫҲе°‘дәәжңғиёҸеҮәиҮӘе·ұзҡ„иҲ’йҒ©еңҲпјҢеӢҮж•ўжҺўзҙўиҮӘе·ұзҡ„еҝ—и¶ЈгҖҒиғҪеҠӣпјҢд№ғиҮіж–јжҘөйҷҗгҖӮиЁұеӨҡдәәеҚідҪҝеӯёжҘӯгҖҒе·ҘдҪңдёҖеҲҮй ҶеҲ©пјҢдҪҶеҚ»зјәд№ҸдҪңзӮәдёҖеҖӢдәәпјҢе°ҚиҮӘе·ұжҮүжңүзҡ„иӘҚиӯҳгҖӮжҜҸеӨ©йҒҺи‘—дё–дҝ—иӘҚе®ҡзҡ„гҖҢеҘҪгҖҚдәәз”ҹпјҢеҚ»дёҚзҹҘйҒ“д»ҖйәјжүҚжҳҜиҮӘе·ұжғіиҰҒзҡ„гҖҢеҘҪгҖҚдәәз”ҹгҖӮ
ж–јжҳҜпјҢеңЁдёҖеҲҮиІҢдјјй ҶеҲ©зҡ„дәәз”ҹдёӯпјҢиЁұеӨҡдәәдёҚж–·е•ҸиҮӘе·ұпјҡгҖҢйҖҷзңҹзҡ„жҳҜжҲ‘иҰҒзҡ„дәәз”ҹе—ҺпјҹгҖҚгҖҢжҲ‘зңҹзҡ„иҰҒйҖҷжЁЈдёҖзӣҙйҒҺдёӢеҺ»пјҹгҖҚгҖҢжҲ‘當еҲқеҰӮжһңжҸӣдёҖжўқи·ҜпјҢдәәз”ҹжңғдёҚжңғжӣҙеҝ«жЁӮпјҹгҖҚ
еҫҲжӮІе“Җзҡ„пјҢйҖҷжЁЈзҡ„е•ҸйЎҢжҳҜжІ’жңүзӯ”жЎҲзҡ„гҖӮеӣ зӮәдәәз”ҹж°ёйҒ йғҪз„Ўжі•йҮҚдҫҶпјҢжІ’жңүдәәиғҪеӣһзӯ”пјҢ當еҲқеҰӮжһңеҒҡеҲҘзҡ„йҒёж“ҮпјҢдәәз”ҹжҳҜеҗҰе°ұжңғжӣҙеҘҪпјҹжӣҙжӮІе“Җзҡ„жҳҜпјҢйҡЁи‘—е№ҙзҙҖж—Ҙй•·пјҢдәәж„ҲжҳҜж”ҫдёҚй–ӢгҖҒж„ҲдёҚж•ўжӢӢжЈ„зңјеүҚзҡ„дёҖеҲҮеҺ»жҺўзҙўеҫһжңӘзҷјзҸҫйҒҺзҡ„иҮӘе·ұгҖӮжңҖеҫҢпјҢдәәз”ҹеҸӘеҘҪеҫ—йҒҺдё”йҒҺпјҢж—Ҙж—ҘеҝҚеҸ—и‘—з„ЎеҘҲгҖҒжҮҠжӮ”пјҢиҲҮиҮӘжҲ‘иіӘз–‘зҡ„з…ҺзҶ¬гҖӮз°ЎзӣҙжҳҜз„Ўй–“ең°зҚ„......
дҪҶе®үе©·йҒёж“Үзҡ„и·ҜпјҢиҲҮиЁұеӨҡдәәдёҚеҗҢгҖӮеҘ№зҡ„дәәз”ҹпјҢеҫһе°ҸжҷӮеҖҷдҫҝе……ж»ҝдәҶжҢ‘жҲ°гҖӮеңЁе°Ҹеӯёзҡ„жҷӮеҖҷпјҢдҫҝиҮӘе·ұдёҖеҖӢдәәйҒ жёЎйҮҚжҙӢеҸғеҠ еӨҸд»ӨзҮҹгҖӮеҺ»зҫҺеңӢи®ҖжӣёжҷӮпјҢжҡ‘еҒҮиҮӘйЎҳеҺ»иҝҰзҙҚгҖҒжө·ең°зӯүең°еҸғиҲҮеҝ—е·Ҙе·ҘдҪңгҖӮз”ҡиҮіпјҢе®үе©·йӮ„иҮӘйЎҳе ұеҗҚеҺ»зңҫдәәиҒһд№ӢиүІи®Ҡзҡ„зҫҺеңӢзӣЈзҚ„пјҢж•ҷдәҶе…©е№ҙеҚҠзҡ„жӣёгҖӮеңЁеҘ№з”Ёеҝғй«”жңғиЁұеӨҡйқһжҲ‘ж—ҸйЎһзҡ„зҠҜдәәзҡ„жҲҗй•·иғҢжҷҜи·ҹеҝғеўғеҫҢпјҢйҖҸйҒҺй»һй»һж»ҙж»ҙзҡ„д»ҳеҮәпјҢжңүдёҖеӨ©и®“д»–еҖ‘жү“й–ӢеҝғжүүгҖҒзңҹжӯЈеҫһеҝғжҠҠеҘ№з•¶жҲҗиҖҒеё«гҖӮ
зңӢдәҶе®үе©·зҡ„ж•…дәӢпјҢдҪ е°ұжңғдәҶи§ЈзӮәд»ҖйәјеҘ№жңғйҒёж“ҮеӣһеҸ°зҒЈпјҢиө°дёҖжўқиүұиҫӣеҚ»е……ж»ҝж„Ҹзҫ©зҡ„дәәз”ҹйҒ“и·ҜгҖӮеӣ зӮәеңЁдёҖеҖӢдёҚж–·жҢ‘жҲ°иҮӘжҲ‘жҘөйҷҗгҖҒиҝҪжұӮеҲ©д»–зҡ„дәәз”ҹдёӯпјҢеҖӢдәәзҡ„з”ҹе‘ҪжүҚжңүж©ҹжңғеҫ—еҲ°жңҖеӨ§зҡ„еҜҰзҸҫгҖӮ
當йқ’е№ҙжңӢеҸӢеңЁзңӢе®үе©·зҡ„ж•…дәӢжҷӮпјҢи«ӢдёҚиҰҒиҝ·еӨұеңЁеҘ№еңЁдёҖж¬Ўж¬ЎйӣЈй—ңд№ӢеҫҢд»Өдәәй©ҡеҳҶзҡ„жҲҗжһңгҖӮи«ӢжҠҠз„Ұй»һж”ҫеңЁз•¶еҘ№жҜҸж¬ЎеҒҡдёҚжӣҫеҒҡйҒҺзҡ„еҳ—и©ҰжҷӮпјҢеҘ№е…§еҝғд№ӢдёӯжүҖж„ҹеҸ—еҲ°зҡ„зЁ®зЁ®з„Ұж…®пјҢд»ҘеҸҠеҰӮдҪ•и·Ңи·Ңж’һж’һиө°еҮәйҖҷдәӣз„Ұж…®зҡ„жӯ·зЁӢгҖӮж…ўж…ўзҡ„пјҢдҪ жңғзҷјзҸҫпјҢе…¶еҜҰе®үе©·иғҪеҒҡеҲ°зҡ„пјҢдҪ д№ҹиғҪеҒҡеҲ°пјҒдҪ жүҖйңҖиҰҒзҡ„пјҢеғ…еғ…жҳҜйЎҳж„ҸиёҸеҮәеҺ»зҡ„еӢҮж°ЈпјҢд»ҘеҸҠдёҖйЎҶзңҹиӘ зӮәдәәзҡ„еҝғгҖӮ
жғіи·ҹе®үе©·дёҖжЁЈжүҫеҲ°дәәз”ҹзҡ„ж„Ҹзҫ©е—Һпјҹ
All you need is some courage!!
жҺЁи–ҰзәҢдёү
жҲҗзӮәжңү擔當зҡ„е№ҙиј•дәә
еҸІеқҰеҲ©пјҺеҚЎиҢІпјҲStanley N. KatzпјүпјҢжҷ®жһ—ж–Ҝй “еЁҒзҲҫйҒңеңӢйҡӣиҲҮе…¬е…ұдәӢеӢҷеӯёйҷўж•ҷжҺҲ
иғҪеӨ зӮәжҲ‘зҡ„еӯёз”ҹеҠүе®үе©·ж–°жӣёиІўзҚ»жҲ‘з°Ўзҹӯзҡ„еәҸж–ҮпјҢжҳҜжҲ‘зҡ„жҰ®е№ёгҖӮжҲ‘жҳҜеңЁдёүгҖҒеӣӣе№ҙеүҚиӘҚиӯҳе®үе©·зҡ„пјҢ當жҷӮеҘ№йҒёдҝ®дәҶжҲ‘еңЁжҷ®жһ—ж–Ҝй “й–Ӣзҡ„з ”з©¶жүҖиӘІзЁӢгҖҢе…¬ж°‘зӨҫжңғиҲҮе…¬е…ұж”ҝзӯ–гҖҚгҖӮйҖҷеҖӢиӘІзЁӢжҳҜй—ңж–је…¬ж°‘зӨҫжңғзҡ„ж©ҹеҲ¶еҰӮдҪ•и®“ж°‘дё»зӨҫжңғжҲҗй•·в”Җв”Җе°Өе…¶жҳҜй—ңж–јйқһзҮҹеҲ©зө„з№”гҖӮе®үе©·йӣ–жҳҜйҖҷй–ҖиӘІдёӯжңҖе№ҙиј•зҡ„еӯёз”ҹпјҢиЎЁзҸҫеҚ»йқһеёёе„Әз§ҖгҖӮеҘ№жҳҺйЎҜе°Қж–је…¬ж°‘иЎҢеӢ•еҰӮдҪ•дҝғйҖІеҗҲдҪңиЎҢзӮәиҲҮйҷҚдҪҺзӨҫжңғиЎқзӘҒжңүж·ұеҺҡзҡ„иҲҲи¶ЈгҖӮеҘ№зҡ„жңҹжң«е ұе‘ҠжҳҜй—ңж–јеңЁжө·ең°зҡ„еҝ—е·ҘиҲҮе®—ж•ҷзө„з№”еңЁжө·ең°зҒҪеҫҢйҮҚе»әзҡ„и§’иүІгҖӮйҖҷеҖӢжҷӮеҖҷпјҢеҘ№е·Із¶“иҠұжҷӮй–“е…ҲеӯёдәҶжі•ж–ҮгҖӮеңЁйҖҷеҖӢйҡҺж®өпјҢеҘ№йӮ„й —зӮәзҫһжҫҖпјҢеӣ жӯӨжҲ‘жІ’жңүж©ҹжңғеҘҪеҘҪиӘҚиӯҳеҘ№пјҢйӣ–然йӮЈй–ҖиӘІеҸӘжңүдәҢеҚҒеҖӢеӯёз”ҹпјҢе…¶дёӯеӨ§еӯёйғЁзҡ„еҸӘжңүе…©дҪҚгҖӮ
еңЁе®үе©·еӨ§дёүе°ҫиҒІпјҢеҘ№дҫҶеҲ°жҲ‘зҡ„иҫҰе…¬е®ӨпјҢе•ҸжҲ‘жҳҜеҗҰиғҪеҒҡеҘ№зҡ„еӨ§еӣӣи«–ж–ҮжҢҮе°Һж•ҷжҺҲгҖӮеңЁжҷ®жһ—ж–Ҝй “пјҢжүҖжңүеӨ§еӣӣз”ҹйғҪиў«иҰҒжұӮиҰҒеҜ«дёҖд»Ҫз ”з©¶и«–ж–ҮпјҢйҖҡеёёй•·еәҰеңЁ100иҮі120й Ғе·ҰеҸігҖӮйҖҷд»Ҫи«–ж–ҮжҳҜдёҖеҖӢйқһеёёеӨ§зҡ„е·ҘзЁӢпјҒеҘ№еҺҹжң¬зҡ„иЁҲз•«жҳҜе…Ҳз”Ёжҡ‘еҒҮеңЁж—Ҙе…§з“ҰеҜҰзҝ’пјҢеҗҢжҷӮ延伸еҘ№е°Қж–јжө·ең°зҡ„иҲҲи¶ЈпјҲд№ҹеҸҜдҪҝз”ЁеҘ№зҡ„жі•ж–ҮпјүгҖӮдҪҶжҳҜеҘ№ж—Ҙе…§з“Ұзҡ„дё»з®Ўе»әиӯ°еҘ№еҺ»зңӢзңӢйқһж”ҝеәңзө„з№”еңЁжҹ¬еҹ”еҜЁзҡ„и§’иүІпјҢ經йҒҺиЁұеӨҡжҖқиҖғеҫҢпјҢе®үе©·еңЁеӨҸеӨ©зҡ„е°ҫиҒІжҗӯдёҠдәҶйЈӣж©ҹпјҢдҫҶеҲ°йҮ‘йӮҠгҖӮ
еңЁйӮЈиЈЎпјҢеҘ№зҷјзҸҫдәҶиЁұеӨҡйқһзҮҹеҲ©зө„з№”жӯЈеңЁеҒҡдёҖдәӣйқһеёёйҮҚиҰҒзҡ„гҖҒйҮҚзө„жҹ¬еҹ”еҜЁзӨҫжңғзҡ„е·ҘдҪңгҖӮдҪҶжҳҜеҘ№д№ҹеҗҢжҷӮзҷјзҸҫйҰ–зӣёжҙӘжЈ®пјҲHun SenпјүиҲҮд»–зҡ„ж”ҝеәңе°Қж–јйҖҷдәӣйқһзҮҹеҲ©зө„з№”иҲҮд»–еҖ‘зҡ„йӣҮе“ЎпјҲдёҚ論當ең°жҲ–еӨ–еңӢпјүйғҪйқһеёёдёҚеҸӢе–„пјҢеӣ зӮәд»–еҖ‘еЁҒи„…дәҶйҖҷеҖӢж”ҝж¬Ҡзҡ„е°Ҳж¬ҠжҺ§еҲ¶гҖӮеӣ жӯӨе®үе©·зҷјеұ•дәҶйҖҷд»Ҫи«–ж–Үзҡ„дё»и»ёпјҢе°ҲжіЁеңЁжӯӨж”ҝж¬ҠеӨҡж¬Ўеҳ—и©ҰйҖҡйҒҺйҷҗеҲ¶йқһзҮҹеҲ©ж©ҹж§Ӣзҡ„жі•жЎҲзҡ„йҒҺзЁӢдёҠпјҢдёҰдё”еҶҚж¬ЎеӣһеҲ°жҹ¬еҹ”еҜЁеҺ»иЁӘе•ҸйқһзҮҹеҲ©ж©ҹж§Ӣй ҳиў–еҖ‘гҖӮжңҖеҫҢпјҢеҘ№еҜ«еҮәдәҶдёҖд»ҪдёҚеҗҢеҮЎйҹҝзҡ„и«–ж–ҮпјҢдёҰдё”еңЁз•ўжҘӯжҷӮзҚІеҫ—дәҶеЁҒзҲҫйҒңеӯёйҷўзҡ„и«–ж–ҮзҚҺгҖӮеҫһжҹ¬еҹ”еҜЁеҲ°еңӢйҡӣзҡ„и®ҖиҖ…йғҪй©ҡиЁқж–јеҘ№еңЁзҹӯжҷӮй–“е…§жүҖзңӢиҰӢзҡ„ж·ұеәҰпјҢд»ҘеҸҠеҘ№еҰӮдҪ•зІҫй—ўеҲҶжһҗж”ҝеәңиҲҮйқһзҮҹеҲ©зө„з№”д№Ӣй–“зҡ„иЎқзӘҒгҖӮ
еҫһжҷ®жһ—ж–Ҝй “з•ўжҘӯд№ӢеҫҢпјҢе®үе©·жұәе®ҡз•ҷеңЁзҫҺеңӢпјҢйӣ–然жҲ‘й»ҳй»ҳзҡ„еёҢжңӣеҘ№жңғеӣһеҸ°зҒЈгҖӮеҘ№еңЁжҷ®жһ—ж–Ҝй “ж“”д»»дёҖеҖӢе•ҶжҘӯз®ЎзҗҶйЎ§е•ҸпјҢиҖҢжҲ‘иӘҚзӮәеҘ№еңЁйӮЈе№ҙеўһеҠ дәҶйқһеёёеӨҡй—ңж–је•ҶжҘӯй ҳеҹҹзҡ„дәҶи§ЈгҖӮдҪҶжҳҜеҘ№дёҰдёҚиҰәеҫ—йЎ§е•Ҹе·ҘдҪңзӮәеҘ№зҡ„з”ҹе‘Ҫеё¶дҫҶж»ҝи¶іпјҢеӣ жӯӨеҘ№й–Ӣе§ӢжҖқзҙўпјҢд№ҹй–Ӣе§ӢиҲҮзҲ¶жҜҚиЁҺи«–жҳҜеҗҰи©ІеӣһеҸ°зҒЈгҖӮзҫҺеңӢзҡ„ж•ҷиӮІж”№йқ©жҳҜжҲ‘зҡ„з ”з©¶иҲҲи¶Јд№ӢдёҖпјҢеҘ№д№ҹиҲҮжҲ‘иЁҺи«–жҳҜеҗҰжңүеҸҜиғҪе°ҮзҫҺеңӢзҡ„дёҖдәӣеүөж–°её¶еӣһеҸ°зҒЈпјҢе°Өе…¶жҳҜTeach For Americaзҡ„жЁЎејҸпјҢе°Үе„Әз§Җзҡ„еӨ§еӯёз•ўжҘӯз”ҹеҲҶжҙҫеҲ°е…¬з«Ӣеӯёж Ўд»»ж•ҷгҖӮй•·и©ұзҹӯиӘӘпјҢеҘ№жҗ¬еӣһеҸ°зҒЈпјҢдёҰдё”еңЁзҲ¶жҜҚйј“еӢөдёӢпјҢй–Ӣе§Ӣеҳ—и©ҰеӢҹж¬ҫж”ҜжҢҒж•ҷиӮІеүөж–°зҡ„еҸҜиғҪгҖӮйҖҷжЁЈзҡ„жҺўзҙўиҲҮеҠӘеҠӣжҲҗе°ұдәҶTeach For Taiwanзҡ„й–Ӣе§Ӣв”Җв”ҖдёҖеҖӢ全然еӣ 著當ең°йңҖжұӮиҲҮзӢҖжіҒж”№и®ҠгҖҒеүөж–°зҡ„жЁЎејҸгҖӮ
е°ҚжҲ‘иҖҢиЁҖпјҢе®үе©·дёҖзӣҙйғҪжҳҜеҖӢе…ёзҜ„еӯёз”ҹгҖӮжҳҺйЎҜзҡ„пјҢеҘ№жҘөз«ҜиҒ°жҳҺгҖҒе–„иЁҖпјҲиҮіе°‘дёүеҖӢиӘһиЁҖпјүгҖҒжңүжҙ»еҠӣпјҢеҸҲжңүеүөжҘӯ家зІҫзҘһгҖӮеңЁжҺҘдёӢдҫҶзҡ„е№ҫе№ҙпјҢTeach For TaiwanеҫҲжңүеҸҜиғҪжңғжҲҗзӮәдёҖеҖӢйқһеёёйҮҚиҰҒзҡ„зө„з№”гҖӮжІ’йҢҜпјҢдёҖеҖӢйҖҷйәје№ҙиј•зҡ„дәәиғҪеӨ еңЁйҖҷйәјзҹӯзҡ„жҷӮй–“е…§жҲҗе°ұйҖҷйәјеӨҡпјҢжҳҜдёҖ件дёҚеҸҜжҖқиӯ°зҡ„дәӢжғ…гҖӮдҪҶе®үе©·зңҹжӯЈдёҚеҮЎзҡ„ең°ж–№пјҢеңЁж–јеҘ№зёҪжҳҜз”ЁеҝғеҸҚжҖқеҘ№зҡ„з”ҹе‘Ҫж—…зЁӢгҖӮжҲ‘йӣ–з„Ўжі•и®ҖжҮӮдёӯж–ҮпјҲе”үпјҒйӣ–然жҲ‘жңүж•ҙд»Ҫж–ҮзЁҝпјҒпјүпјҢдҪҶжҲ‘зўәдҝЎеҘ№зҡ„дёӯж–ҮеҜ«дҪңеҝ…е®ҡиҲҮеҘ№зҡ„иӢұж–ҮеҗҢжЁЈе„Әйӣ…гҖӮжҲ‘еёҢжңӣеҘ№зҡ„ж•…дәӢиғҪжҝҖеӢөе…¶д»–иҒ°жҳҺгҖҒе°ҚзӨҫжңғжңүиІ ж“”зҡ„еҸ°зҒЈе№ҙиј•дәәпјҢзӮәи‘—дҪ еҖ‘зҡ„еңӢ家民主зҡ„жңӘдҫҶд»ҳеҮәдҪ еҖ‘зҡ„з”ҹе‘ҪпјҢе°ұеҰӮеҗҢе®үе©·еӢҮж•ўгҖҒзҙ°иҶ©зҡ„жӯЈеңЁеҒҡзҡ„гҖӮBravo!
пјҲиӢұж–Үе…Ёж–Үпјү
It is a pleasure for me to contribute this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written by my student An-ting Liu. I first met An-ting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when she enrolled in my undergraduate cours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on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Policy. This is a course on how democratic societies hold themselves together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civil society – mainly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ting was one of the best students in the course even though she was one of the youngest. She was clearly deeply interested in how social activity facilitates cooperative behaviors and diminishes social conflict. She wrote her term paper on the role of voluntary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providing relief in Haiti. And at this point she managed to learn French. She was at that stage quite shy, however, and I did not get to know her very well even in a group of 20 or 2 students.
But at the end of An-ting’s third year of college she approached me and asked if I would supervise her senior thesis – at Princeton all seniors are required to write a research paper that usually runs from 100 to 120 pages in length. The senior thesis is a major undertaking! Her plan was to work in Geneva, Switzerland for the summer, and to develop a thesis project out of her interest in Haiti (and thereby to use her French). But her supervisor in Geneva suggested that the role of 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ambodia might be more interesting to study. And so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An-ting got on a plane and went to see what was happening in Pnom Phen.
There she discovered that NGOs, especially those funded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were doing very important work in reconstituting Cambodian society. But she also discovered that Prime Minister Hun Sen and his government were quite hostile to the NGOs and their employees (whether indigenous or foreigners), since they threatened the autocratic control of the Hun Sen regime. So An-ting formulated a thesis on the attempts of the regime to pass legislation restricting the role of NGO, and traveled again to Cambodia to interview NGO leaders. The result was an exceptional thesis that won a prize from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when An-ting graduated. Readers both in Cambodia and internationally were astonished at how much she had been able to learn, and how brilliantly she analyz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GOs and the government.
After graduating from Princeton, An-ting decided to re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though I had hoped she would return to Taiwan. She took a job as a business consultant here in Princeton, and I think she learned a great deal about the commercial sector that year. But she did not find consulting a very fulfilling role in life, and she began to think (and to discuss with her parents) what she might do if she returned to Taipei. Schoo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one of my interests, and she discussed with me the possibility of adapting U.S. models of reform (primarily the approach used here by Teach for America, which recruits bright college graduates to teach in public schools) to be used in Taiwan. So she moved back to Taipei and,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her parents, began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beginning a privately-funded school reform program at home. This has led to her establishment of Teach for Taiwan, a fully origi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ch For” model to Taiwan.
An-ting for me has been the model student. She is, obviously, extremely bright and articulate (in at least three languages), energetic and entrepreneurial. Teach for Taiwan is likely to be a very important organizati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such a young person should achieve so much so quickly. But what is truly exceptional is that An-ting is so reflective about her life’s journey. I do not read Mandarin, alas, so I have not read this text (although I have a copy!), but I feel certain that An-ting writes as elegantly in Mandarin as she does in English. And I hope her story will motivate other bright and socially engaged young men and women in Taiwan to commit their lives to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your country in the brave and thoughtful manner that An-ting has done. Bravo!
дҪңиҖ…иҮӘеәҸ
иҮҙжҲ‘зҡ„зҲ¶жҜҚ
ж„ӣдёҚжҳҜжҲ‘еҖ‘иҰҒеҺ»зҡ„ж–№еҗ‘пјҢиҖҢжҳҜжҲ‘еҖ‘еҮәзҷјзҡ„ең°ж–№в”Җв”Җеҫҗи¶…ж–ҢйҶ«её«
дәҢв—ӢдёҖдәҢе№ҙеҚҒдёҖжңҲеә•пјҢжҲ‘йӮ„еңЁзҫҺеңӢзҡ„йЎ§е•Ҹе…¬еҸёдёҠзҸӯпјҢжүӢж©ҹгҖҢеҸ®е’ҡгҖҚйҹҝдәҶдёҖиҒІпјҢжҲ‘зңӢиҰӢеӘҪеӘҪеҜ«зҡ„гҖҢйҳҝе¬Ө已經еңЁжҳЁеӨ©дёӢеҚҲе®үи©ізҡ„еӣһеҲ°еӨ©е®¶гҖҚпјҢи…ҰдёӯеҝҪ然дёҖзүҮз©әзҷҪгҖӮ
йҡ”дәҶдёҚеҲ°е…©йҖұпјҢжҲ‘йЈӣеӣһеҸ°зҒЈпјҢдёҖдёӢйЈӣж©ҹдҫҝзӣҙеҘ”еӨ–е©Ҷзҡ„е–ӘзҰ®гҖӮе–ӘзҰ®зөҗжқҹд№ӢеҫҢпјҢжҲ‘еҖ‘еӣһеҲ°еӨ–е©Ҷ家гҖӮеӨ–е©Ҷзҡ„еӣӣеҖӢеҘіе…’жҠҠжүҖжңүеӯ«е…’иј©иҒҡйӣҶиө·дҫҶпјҢе‘ҠиЁҙжҲ‘еҖ‘еҸҜд»ҘиҠұдәӣжҷӮй–“еңЁеӨ–е©ҶжҲҝй–“иЈЎжүҫдёҖжЁЈжңҖеҸҜд»ҘзҙҖеҝөеӨ–е©Ҷзҡ„зү©е“ҒпјҢеё¶и‘—иө°гҖӮ
жҲ‘дёҖеҖӢз®ӯжӯҘи·‘еҲ°еӨ–е©ҶеәҠйӮҠпјҢжӢҝиө·еҘ№зҡ„иҒ–經гҖӮеӨ–е©ҶжҳҜ家дёӯ第дёҖеҖӢеҹәзқЈеҫ’пјҢдёҖиј©еӯҗйғҪз”ЁеҗҢдёҖжң¬иҒ–經пјҢеӣ жӯӨжҲ‘дёҖзӣҙе°Қе®ғжҠұи‘—еҫҲж·ұзҡ„еҘҪеҘҮгҖӮжү“й–ӢиҒ–經пјҢеҫһжӣёиғҢж»‘еҮәдёҖејөй»ғиүІзҡ„дҝЎзҙҷгҖӮжҲ‘жҠҠе®ғжӢҝиө·дҫҶзңӢпјҢзҷјзҸҫйҖҷжҳҜеӨ–е©ҶеңЁеӨ–е…¬еҚҒеӨҡе№ҙеүҚйҒҺдё–еҫҢзҡ„第дёҖеҖӢжё…жҳҺзҜҖпјҢеҜ«зөҰдёҠеёқзҡ„дёҖе°ҒдҝЎгҖӮ
еӨ–е©ҶеңЁдё–жҷӮжҳҜеҖӢеј·йҹҢгҖҒдёҚиј•жҳ“иЎЁйңІжғ…ж„ҹзҡ„еҘіеј·дәәпјҢдҪҶеңЁйҖҷиЈЎпјҢеҘ№з”ЁеЁҹз§Җзҡ„еӯ—и·ЎеҜ«и‘—пјҡ
иҰӘж„ӣзҡ„дё»дёҠеёқпјҢиӨҮдёҖж¬ЎдҪҮ祢йқўеүҚжҮҮжұӮпјҢз…§祢иұҗзӣӣзҡ„з–јз—ӣпјҢеј•е°ҺеҘіе©ўе…Ёе®¶иЎҢдҪҮ祢е…¬зҫ©зҡ„йҒ“и·ҜпјҢе …еӣәйҳ®е°Қ祢зҡ„дҝЎд»°пјҢи®ҠеҢ–еҘіе©ўе°Қе…ҲеӨ«зҡ„жҖқеҝөпјҢжңүеұ¬еӨ©зҡ„жҷәж…§иҲҮж°ЈеҠӣ……дә’йҳ®з”Ёеҝ еӯқеӮіе®¶пјҢиө·йҖ е’Ң諧зҡ„家еәӯ……жұӮдё»з№јзәҢжү¶жҢҒзҘқзҰҸйҳ®зҡ„家ж—ҸпјҢз„Ўи«–дҝЎд»°гҖҒдҪҮз”ҹжҙ»гҖҒдҪҮдәӢжҘӯгҖҒе·ҘдҪңгҖҒжҲ–иҖ…еӯёжҘӯеҠҹиӘІгҖҒеәҸе°Ҹзҡ„ж Ҫеҹ№пјҢж”Ҹжңғеҫ—祢еј•е°Һ……е……ж»ҝе–ңжЁӮиҲҮе№іе®үгҖӮ
и®ҖеҲ°йҖҷиЈЎпјҢеҺҹжң¬еңЁе–ӘзҰ®йӮ„еј·еҝҚи‘—дёҚе“ӯзҡ„жҲ‘пјҢеҝҚдёҚдҪҸз•ҷдёӢдёҖж»ҙж»ҙж„ҹжҒ©зҡ„ж·ҡж°ҙгҖӮжҲ‘зҡ„еӨ–е©ҶжІ’жңүз•ҷзөҰжҲ‘йҮ‘йҠҖзҸ еҜ¶пјҢдҪҶжҳҜеҚ»з•ҷзөҰжҲ‘жңҖз„Ўеғ№зҡ„еҜ¶и—ҸпјҡдёҖд»Јд»ЈеӮіжүҝгҖҒеңЁиүұиӢҰдёӯд»Қ然жҢҒе®Ҳзҡ„ж„ӣгҖӮ
еӣ и‘—еҜ«йҖҷжң¬жӣёпјҢжҲ‘жңүж©ҹжңғе’ҢиҮӘе·ұдёҖиө·йҮҚж–°еӣһйЎ§йҒҺеҺ»е№ҫе№ҙжүҖ經жӯ·зҡ„жҜҸдёҖжӯҘгҖӮеүӣй–Ӣе§ӢеҜ«жҷӮпјҢжҲ‘д»ҘзӮәйҖҷжң¬жӣёжҳҜй—ңд№ҺиҮӘе·ұеӯёзҝ’зҚЁз«Ӣзҡ„йҒҺзЁӢгҖӮ然иҖҢпјҢ當жҲ‘зҙ°зҙ°жҖқжғіпјҢжҲ‘жүҚж„ҸиӯҳеҲ°пјҢзӣёеҸҚзҡ„пјҢеҮәиө°и®“жҲ‘зңӢиҰӢиҮӘе·ұжҳҜеӨҡйәјзҡ„и»ҹејұпјҢеҚ»д№ҹжҳҜеңЁйҖҷдәӣи»ҹејұд№ӢдёӯпјҢзңӢиҰӢиғҢеҫҢжүҖж”ҜжҢҒжҲ‘зҡ„ж„ӣжҳҜеӨҡйәјзҡ„з„Ўжўқ件гҖҒе§ӢзөӮдёҚи®ҠгҖӮ
жҲ‘зҡ„зҲ¶жҜҚдёҚеёёз”ЁиЁҖиӘһеҺ»жҸҸз№Әд»–еҖ‘е°ҚжҲ‘зҡ„ж„ӣпјҢдҪҶжҳҜжҲ‘е§ӢзөӮиЁҳеҫ—пјҢжңүдёҖж¬ЎпјҢеӨңж·ұдәәйқңжҷӮпјҢжҲ‘зҡ„зҲёзҲёеЁ“еЁ“е‘ҠиЁҙжҲ‘еңЁд»–еҝғдёӯйӣЈд»ҘзЈЁж»…зҡ„дёҖ幕пјҡеңЁжҲ‘еҚҮе°Ҹеӯёд№ӢеүҚзҡ„йӮЈеҖӢжҡ‘еҒҮпјҢ家裡зҡ„經жҝҹеҮәзҸҫдәҶеҫҲеӨ§зҡ„йӣЈиҷ•пјҢеӣ жӯӨжҲ‘еҖ‘еҝ…й Ҳжҗ¬еҲ°ж°ёе’ҢдёҖй–“йқһеёёе°ҸгҖҒйқһеёёз ҙиҲҠзҡ„е®ҝиҲҚдёӯгҖӮзӮҺзҶұзҡ„еӨҸеӨ©иЈЎпјҢзҲёзҲёеё¶и‘—жҲ‘пјҢжҸҗи‘—дёҖжЎ¶зҷҪиүІжІ№жјҶпјҢйҮҚж–°зІүеҲ·жүҖжңүзүҶеЈҒгҖӮйӮЈжҷӮпјҢжҗһдёҚжё…жҘҡзҷјз”ҹд»ҖйәјдәӢжғ…зҡ„жҲ‘пјҢзңӢи‘—ж–‘й§Ғзҡ„зүҶеЈҒгҖҒж»ҝең°иһһиҹ»гҖҒжӯ»иҹ‘иһӮпјҢе°ҸиҒІзҡ„е•Ҹд»–пјҡгҖҢзҲёзҲёпјҢжҲ‘еҖ‘еҸҜдёҚеҸҜд»ҘдёҚиҰҒжҗ¬еҲ°йҖҷиЈЎпјҹгҖҚ
зҲёзҲёи¬ӣеҲ°йҖҷиЈЎжҷӮпјҢзңјзқӣеҝҪ然充ж»ҝдәҶж·ҡж°ҙпјҢиӘӘпјҡгҖҢйӮЈжҷӮеҖҷпјҢжҲ‘дҫҝдёӢе®ҡжұәеҝғпјҢз”ҹжҙ»еҶҚжҖҺйәјиӢҰпјҢжҲ‘йғҪиҰҒи®“еҰіе№ёзҰҸпјҢжүҖд»ҘжҲ‘е‘ҠиЁҙеҰіпјҡгҖҺе®үе©·пјҢдёҚиҰҒж“”еҝғпјҢзҲёзҲёдҝқиӯүпјҢдҪҸеңЁйҖҷиЈЎзҡ„ж—ҘеӯҗжңғжҳҜжңҖеҝ«жЁӮзҡ„пјҒгҖҸгҖҚ
еҜ«йҖҷжң¬жӣёжҷӮпјҢжҲ‘жҷӮеёёдёҚзҹҘйҒ“и©ІеңЁе“ӘиЈЎжҠҠжҲ‘зҡ„家дәәеҜ«йҖІеҺ»в”Җв”Җз•ўз«ҹпјҢдёҚз®ЎжҳҜеңЁзҫҺеңӢгҖҒиҝҰзҙҚгҖҒжө·ең°гҖҒйӮ„жҳҜжҹ¬еҹ”еҜЁпјҢд»–еҖ‘зҗҶи«–дёҠйғҪжІ’жңүи·ҹжҲ‘еңЁдёҖиө·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жҳҜйҖҷдёҖе°ҚеҚідҪҝеңЁжңҖиҫӣиӢҰзҡ„жҷӮеҖҷпјҢд»Қз„¶е …жҢҒзөҰжҲ‘жңҖйЈҪж»ҝзҡ„ж„ӣзҡ„зҲ¶жҜҚпјӣеҰӮжһңдёҚжҳҜд»–еҖ‘жҜҸдёҖеӨ©дёҚеҒңжӯўзӮәжҲ‘зҡ„зҰұе‘ҠгҖҒдёҚжҳҜд»–еҖ‘еңЁжҲ‘зҠҜйҢҜжҷӮд»Қ然無жўқ件зҡ„жҺҘзҙҚжҲ‘пјҢе‘ҠиЁҙжҲ‘гҖҢеҰіеҫҲзү№еҲҘгҖҚпјҢжҲ‘дёҚеҸҜиғҪжҶ‘и‘—иҮӘе·ұжүҫеҲ°иө°дёӢеҺ»зҡ„еҠӣйҮҸгҖӮд»–еҖ‘зөҰжҲ‘зҡ„еҜ¶и—ҸпјҢжҳҜгҖҢ家гҖҚгҖӮжүҖд»ҘпјҢжңҖзөӮпјҢеҮәиө°пјҢжҳҜеӣ зӮәжңү家пјҢд№ҹжҳҜзӮәдәҶеӣһ家гҖӮ
жҲ‘жұәе®ҡж”ҫжЈ„еҸ°еӨ§гҖҒйӣўй–ӢеҸ°зҒЈзҡ„жҷӮеҖҷпјҢе…Ёдё–з•Ңдјјд№ҺйғҪиҰәеҫ—жҲ‘зҳӢдәҶгҖӮйӮЈжҷӮпјҢжҳҜжҲ‘зҡ„зҲ¶жҜҚзӮәжҲ‘жүӣдёӢеӨ–з•ҢжүҖжңүеЈ“еҠӣпјҢе‘ҠиЁҙжҲ‘пјҡгҖҢзҲёзҲёеӘҪеӘҪжңғзӮәеҰізҰұе‘ҠпјҢжҲ‘еҖ‘зҹҘйҒ“зҘһжңғзөҰеҰіжңҖеҘҪзҡ„гҖӮгҖҚ
дә”е№ҙеҫҢпјҢ當жҲ‘иәҠиәҮдёҚе®ҡпјҢдёҚзҹҘйҒ“жҳҜеҗҰи©Іж”ҫдёӢжҲ‘еңЁзҫҺеңӢзҡ„з”ҹжҙ»пјҢеӣһеҸ°зҒЈеүөз«ӢTeach For TaiwanпјҢжҳҜжҲ‘зҡ„зҲёзҲёи·ҹжҲ‘иӘӘпјҡгҖҢе®үе©·пјҢдёҚиҰҒе®іжҖ•еӨұж•—гҖӮеҰіж—ўз„¶зңӢеҲ°дәҶйңҖиҰҒпјҢе°ұи©ІеӣһдҫҶгҖӮгҖҚ
жҲ‘дёҚзҹҘйҒ“жҳҜеӨҡж·ұзҡ„ж„ӣпјҢи®“д»–еҖ‘еҚідҪҝзҹҘйҒ“иҮӘе·ұзҡ„еӯ©еӯҗжңғеҸ—еӮ·пјҢд»Қ然йЎҳж„Ҹж”ҫжүӢи®“жҲ‘йЈӣгҖӮжҲ‘дёҚзҹҘйҒ“жҳҜеӨҡеӨ§зҡ„ж„ӣпјҢи®“д»–еҖ‘еҚідҪҝиў«е№ҙе°‘з„ЎзҹҘзҡ„жҲ‘жҷӮеёёиҰ–зӮәзҗҶжүҖ當然пјҢд»Қ然йЎҳж„Ҹй»ҳй»ҳеңЁж—©жҷЁеҺ»еёӮе ҙпјҢиІ·дёҖзў—ж–°й®®зҡ„йӣһзІҫеӣһ家пјҢж”ҫеңЁжҲ‘еәҠеүҚпјҢеёҢжңӣжҲ‘еҒҘеә·гҖӮ
жҲ‘зҡ„зҲёеӘҪжІ’жңүй«ҳеӯёжӯ·гҖҒй«ҳеҗҚж°ЈжҲ–жҳҜиІЎз”ўпјҢдҪҶжҳҜд»–еҖ‘з”Ёд»–еҖ‘зҡ„з”ҹе‘ҪзөҰжҲ‘жңҖеј·еӨ§зҡ„еҫҢзӣҫпјҢи®“жҲ‘жңүеҠӣж°ЈгҖҒжңүз©әй–“еҺ»еҶ’йҡӘгҖҒеҺ»жҺўзҙўпјҢеҺ»е“ӯгҖҒеҺ»з¬‘гҖҒеҺ»ж„ӣгҖҒеҺ»з ҙзўҺгҖӮ
дә”е№ҙзҡ„еҮәиө°ж•…дәӢпјҢд№ҹжҳҜдә”е№ҙиҝҪе°Ӣд»ҖйәјжҳҜж„ӣгҖҒеҰӮдҪ•еҺ»ж„ӣзҡ„йҒҺзЁӢгҖӮеӣһй ӯзңӢпјҢжүҚзҷјзҸҫж„ӣдёҚжҳҜжҲ‘иҰҒеҺ»зҡ„ж–№еҗ‘пјҢиҖҢжҳҜжҲ‘еҮәзҷјзҡ„ең°ж–№гҖӮ
д»–еҖ‘зҡ„ж„ӣпјҢе°ұеҰӮеҗҢйҖҷйҰ–и©©жӯҢжүҖеҜ«зҡ„пјҡ
ж„ӣиҰӘеғҸйўЁеҗ№пјҸиј•иј•ж”ҫдә’йҳ®йЈӣпјҸжҜӢз®ЎеӨ©й ӮеҒҢе‘ўй—ҠпјҸжҜӢз®Ўжҝӣйң§еҒҢе‘ўеӨ§пјҸеңЁжҝӣжҝӣзҡ„йўЁйӣЁдёӯпјҸйўЁеҗ№ж°ёйҒ иўӮеӨұиҝ·пјҸиҮӘз”ұе’ҢиҮӘеңЁпјҸж°ёйҒ зүҪи‘—йҳ®зҡ„з·ҡпјҸж°ёйҒ зңӢйЎ§йҳ®
жҲ–иЁұпјҢжҲ‘д№ҹеҫҲеғҸеӨ–е©ҶпјҢеҫҲе°‘иј•жҳ“иЎЁйңІжҲ‘зҡ„жғ…ж„ҹпјҢжҲ‘д№ҹжӣҫ經д»ҘзӮәжҲҗзҶҹзҡ„иЎЁзҸҫдҫҝжҳҜдёҚеҶҚйқ зҲ¶жҜҚгҖӮдҪҶжҳҜзҸҫеңЁпјҢжҲ‘йЎҳйҖҷжң¬жӣёдёҚеҸӘй—ңд№ҺжҲ‘пјҢжӣҙеҗ‘жҲ‘зҡ„зҲ¶жҜҚзҡ„ж„ӣиҲҮжҰңжЁЈзҚ»дёҠж·ұж·ұзҡ„ж„ҹи¬қгҖӮжҳҜд»–еҖ‘зҡ„ж„ӣжҲҗе°ұдәҶжҲ‘зҡ„ж•…дәӢв”Җв”ҖжҲ‘зҡ„ж•…дәӢеҫҲе№іеҮЎпјҢдҪҶд»–еҖ‘зҡ„ж„ӣдёҖй»һйғҪдёҚе№іеҮЎгҖӮ
Nay, in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through Him that loved us. –Romans 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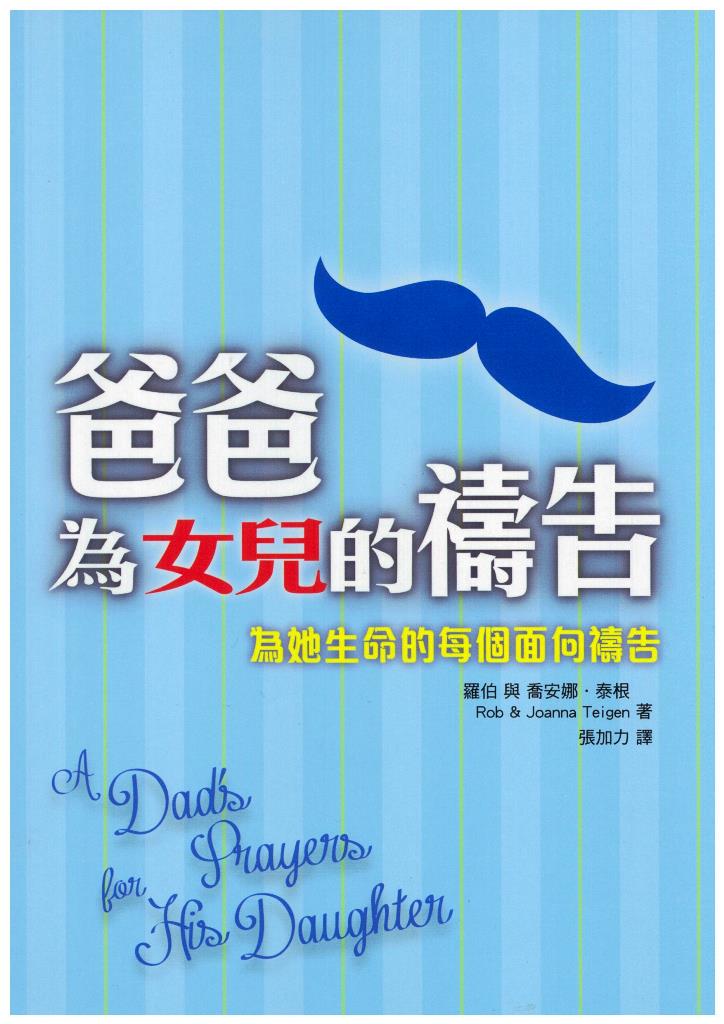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