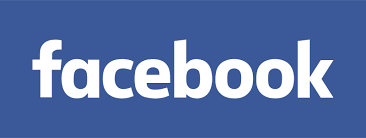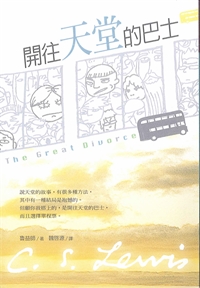但願你我搭上的,是開往天堂的巴士,
而且我們選擇的是單程票。
這個選擇,不僅關乎生死,
更擴及生前與死後的一切。
幽冥城──人死後靈魂的居住地,濕冷蒼茫,廣大無邊。據說幽冥城裡的幽靈,遇假日可以出外旅行,這傳說可信度不小,君不見有的幽靈選擇旅行回到塵世,戲弄靈媒;有的去維護從前房子的主權,所以房子鬧鬼。另有些幽靈,則是搭上開往天堂的巴士,進行「天堂一日遊」。如果你喜歡,可以留下來;如果你不願,可以原車返回。
是什麼樣的天堂,讓嚮往的幽靈望之卻步?是誰在那端等待,令幽靈又憤又惱?是什麼樣的執念,讓整批幽靈不惜折返?是什麼樣的天境,只留得住一縷靈魂?隨著故事一幕幕展開,讀者似也如縷針氈,被迫作出留下或返回的艱難抉擇……
「人若選擇了塵世而非天堂,終將發現塵世一向都只是地獄的一部分;而塵世若被置於天堂之次,則一開始就是天堂本身的一部分。」
「對得救的人而言,不單這山谷,
就連他們過去在世的一切都是天堂。
而在墮入地獄的人眼中看來,不僅幽冥城裡充滿幽暗,
連他們在世的生活也都是地獄。」──摘自第9章
先後任教於英國牛津與劍橋大學,三十三歲成為基督徒,自稱是全英國最不情願的歸信者,後來卻成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護教家。
從未受過神學訓練的魯益師,談論教義的方式反而跳脫傳統思維,在他那「土法煉鋼」的解析之下,同樣的神學命題,卻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例如在本書中,他便充分發揮文學長才,以小說體裁闡明他獨特的「天堂觀」。
魯益師以其靈巧的想像力,跳脫聖經中黃金街、碧玉城的天堂印象,反而建構出一個草堅如剛鑽、雨滴若槍彈、堅不可摧、真實無比的天堂場景;再將塵世的是非恩怨一齣齣搬到天堂邊境。藉著一對對角色的對話,魯益師不僅用力劃出善惡真假的界線,你我所以為的天堂面貌,恐怕也將徹底被顛覆。
譯者簡介
魏啟源
大學主修英美文學,曾任中學英文教師。後來赴美、英攻讀神學,現任中華福音神學院新約副教授。譯作有:《成為神蹟》、《新人》(與陳宗清合譯)、《當代講道藝術》(與劉良淑合譯)、《讀經的藝術》(與饒孝榛合譯)。
推薦序三 天堂地獄跟你想得不一樣 015
自 序 019
第1章 025
第2章 031
第3章 045
第4章 051
第5章 059
第6章 073
第7章 079
第8章 087
第9章 095
第10章 123
第11章 131
第12章 153
第13章 165
第14章 181
3
前面隱約可見一片絕壁,黝黑光滑,峭立千仞,深不見底。我們一直騰空而上。絕壁頂喘終於在望,細細的一線翠綠,宛若拉緊的琴弦。不久我們就滑過了壁頂,飛臨一片平坦的草原。草原上有一條寬闊的河流經其間。我們正往下降落,距離下面一些最高的樹梢只有二十呎。然後驀地停住。大家都跳了起來。這時同行的旅客爭著下車,連打帶罵的喧鬧聲傳到我耳中。一會兒之後,他們都下去了。只有我一人在車裡,清靜之中,雲雀的歌聲從敞開的車門飄了進來。
我出到外邊。天光和涼意迎面襲來,就和夏日清晨破曉前一兩分鐘給人的感覺一樣,只是仍有些微差異。我覺得自己置身於一片極其廣袤的空間,或竟可說是一種較我以前所知更為廣大的空問。比起渺小的地球來說,這裡的天空好像遼闊得多,綠野平疇也更加寬廣。我已經出到「外邊」,就某種意義而言,這使得太陽系似乎成了斗室之物。我感到自由,卻也覺得暴露──可能暴露於某種危險之下──這種感覺後來始終伴著我。我無法表達這種感受,繼續描述時也不可能使你記得這種感受,因此我不敢奢望能將我所見所聞的真實本質傳達出來。
起初我當然先注意那些與我同行的遊客。他們依舊三三兩兩聚在巴士附近。
有些人則開始試著以猶疑的步伐走向前邊的風景。我看著他們,不禁大吃一驚。如今在光中,他們的身子是透明的。站在我與光之間的時候,通體透明;站在樹蔭底下,就朦矇朧朧,模糊不清。原來他們是幽靈──在明亮空氣中的人形陰影。你可以在意他們,也可以不理睬他們,就如你看待玻璃窗上的灰塵一般。我注意到他們腳下的草並沒有彎曲,連露珠也未受攪動。
然後我的心靈發生了某種調整、不然就是我的眼光重新聚焦,於是我看這一切現象的方式完全不同了。這些人就是他們原來的樣子,或許與我所認識的人也一樣,只因為這裡的光、草、樹木是由某種截然不同的物質做成的,比世上的東西堅實得多,所以相形之下,人就成了幽靈。我靈機一動,彎下身來想摘腳下的一朵雛菊,卻怎麼也折不斷。我試著扭斷它,也無法動它分毫。我使勁兒拉,弄得滿頭大汗,雙手也脫去了一大片皮。
那朵小花之堅硬,絕非尋常的木頭鐵塊可比,倒像金剛鑽。花兒旁邊的草上,有一片柔嫩的山毛櫸葉子,我想把它撿起來,卻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勉強擡起一點點,旋即不勝負荷,撒手放下,因為它比一袋煤炭還重。我站著喘息,俯視那朵雛菊,發現我不僅可以看見在我雙腳中間的草,還可以看見我腳底板下的草。原來我也是個透明的幽靈。我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話來表達我內心的震驚,暗想:「哎呀!這下子可糟了。」
有人尖叫著:「我不喜歡!我不喜歡!我討厭這裡!」一個幽靈從我身邊急奔而過,回到車內。據我所知,她再也沒有出來過。
其餘的人雖然留下來了,卻是驚魂不定。
大個子招呼司機道:「嗨,先生,我們幾時要回去?」
司機答說:「你若不想的話,永遠不必回去,你愛留多久就留多久。」接著是一陣令人侷促不安的沈寂。
我耳邊有個聲音響起:「真可笑。」一位較為安靜可敬的幽靈側著身子走到我這裡來,繼續說道:「一定有什麼地方管理不當。讓這群烏合之眾成日在此東飄西蕩,究竟有何意義?瞧瞧他們,他們根本不喜歡這裡,留在家中反而快樂得多。他們甚至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說:「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我們究竟要做什麼?」
「我嗎?等一會兒我就要與某人碰面。有人在等我來。我一點都不必操心。
不過,頭一天就有一大群遊客擠滿這整個地方,確實叫人很不愉快。真要命,到這裡來的主要目的原本就是要避開他們的!」
他從我身邊飄走。我開始環顧四周。儘管他提及「一大群人」,我卻覺得異常孤獨,幾乎沒注意到前面景物中的一群幽靈。綠色和明光差不多將他們都吞沒了。但在遠處,我可以看見一大簇雲,也可能是一列山脈。有時我能隱約辨識出其中險峻的森林,迤邐幽遠的山谷,甚至於無法企及之峯頂上的城市。有時卻只見一片虛無縹緲。由於山勢異常高峻,以至於我矇朧的視線完全無法將景物盡納眼底。明光籠罩山頭,從上方斜射下來,照得平原上的樹木長影橫斜。任憑時光流轉,影子卻沒有什麼變動。黎明的應許──或說威脅,紋絲兒不動地靜止在那山嶺之上。
過了許久,我看見有一群人迎面而來。由於他們渾身是光,我遠遠地就看見他們了。起初我並不知道他們是一群人。他們漸行漸近,健壯的腳踏著潮濕的草地,地為之震動。他們落腳之處,草碎珠零,揚起一陣薄霧馨香。有些人赤身裸體,有些人穿著長袍。但赤身裸體的美毫不遜於華服,而長袍也未能衣服底下肉身的魁偉和肌膚的燦斕光華。有些人蓄著鬍鬚,然而在我看來,他們的年紀並沒有老幼之分。就算在我們的地方,也可以看見無年齡之分的事物,例如嬰兒臉上沉思的樣子,以及老年人臉上天真歡樂的神情。這裡就是這樣。他們平穩地前進。我不十分喜歡那種姿勢。有兩個幽靈驚呼出聲,跑向巴士。我們其餘的人則緊緊地彼此靠攏。
4
這群壯實的人越行越近,我注意到他們行進間秩序井然,步履堅決,好像已各自在我們這群幽靈裡找定了對象。我自忖:「有好戲可看了。不過旁觀也許不好。」如此一想,我便悄悄溜開,想去探險一番。在我右方有一片巨大的香柏樹林,看來頗為引人,我便進到裡面。不料路徑十分難行。地上的草堅似鑽石,我覺得脆弱的雙腳彷彿走在崎嶇不平的巖石上,受著和安徒生童話裡的小人魚一樣的痛苦。有一隻鳥兒從我面前掠過,真令我羨慕。牠屬於這地方,像這裡的草一樣真實,又能折莖濺露。
幾乎同時,那位大個子──說得更確切點,那位大個子幽靈,也跟了過來。
他後面又跟著一個光明的靈,高聲向他招呼:「你不認得我了嗎?」我忍不住回頭看,這個壯實的靈穿著長袍,臉上流露著歡欣和青春的氣息,令人看了直想為之起舞。
大個子幽靈說:「啊!怎麼回事!我才不信,打死我都不相信!連恩,這樣不對你也曉得吧。可憐的傑克要怎麼辦?啊?你看起來滿快活的樣子,但我說哪,可憐的傑克怎麼辦?」
對方說:「他在這裡。你不久就會見到他的,如果你留下來的話。」
「但是你謀殺了他。」
「不錯,我殺了他。但現在沒事了。」
「沒事了,是嗎?你的意思是說,你沒事了。但那個可憐的傢伙怎麼辦呢?他還屍骨未寒呢。」
「他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樣子了。我說過,你不久就會見到他的。他要我向你問安。」
幽靈說:「我想弄清楚你來這裡幹什麼?你這滿手血腥的兇手,看起來倒滿自在的,我這些年來卻一直在那下邊的街上徘徊,住在豬欄一樣的地方。」
「一開始是有點難懂,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你馬上就會喜歡的,到時你就不必再為此煩惱了。」
「不必煩惱?你難道不覺得慚愧嗎?」
「不會,不像你想的那樣,我不再看自己,我已經棄絕自己了。你曉得,殺了人以後,我不得不如此。拜殺人之賜,一切就這樣開始了。」
「依我個人的淺見。」大幽靈特別加重語氣,完全不像在發表「淺見」。「依我個人的淺見,我認為你我的處境應當調換。這就是我的想法。」
對方說:「很可能我們馬上就會這樣,假如你不再那麼想的話。」
幽靈拍拍胸脯(卻無聲響)說:「看看我,我一生為人正直,不是說我是個敬虔的人,也不是說我沒犯過錯,差遠了,但我一輩子努力行善,你明白嗎?我盡力和善待人,我就是這樣。不是我分內的東西我從來不要。叫了喝的,我會付帳,拿了薪水,我就給人辦事,明白嗎?我就是這樣,我也不在乎有誰知道。」
「現在最好別再一直講那些了。」
「誰一直講啊?我不是要和你爭辯,我只是要告訴你我是什麼樣的人,明白嗎?我不求別的,我要的不過是我應得的權利而已。你也許認為憑你這身打扮就能夠壓制我(你在我手下工作的時候,不是穿這個樣子的),而我只是個可憐蟲而已。但我一定要與你一樣得到我應得的權利,明白嗎?」
「喔,不是的,還沒糟到那種地步。我並沒有得著我應得的權利,否則我不會到這裡來。你也不會得到你的權利。你會得著更美好的東西。不要怕。」
「那正是我所說的,我沒有得著我應有的權利。我一向盡力行善,從來沒做過什麼錯事。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我應該屈居像你這樣殘忍的殺人兇手之下。」
「誰曉得你將來會不會呢?你只要快快樂樂地隨我來。」
「你到底在說些什麼?我只是要告訴你我是什麼樣的人,我只要我的權利,我不求任何人該死的憐憫(bleeding charity)。」
「那麼,你最好馬上就求那寶血的憐憫(Bleeding Charity)。1這裡的一切只給尋求的人,不是可以用錢買得到的。」
「我說那倒挺適合你的啊。如果他們竟然願意讓一個殘忍的殺人兇手進來,只因他在最後一刻苦苦哀求,那是他們的事。但我跟你的情況不一樣,明白嗎?憑什麼啊?我才不要人憐憫。我是個清白的人,按我應得的權利來說,我早就該在這裡了。你可以告訴他們我就是這樣說的。」
對方搖了搖頭,說:「你這樣子永遠行不通,你的腳永遠健壯不起來,無法走在我們的草上。你還沒到達山上就會筋疲力盡的。而且,你也曉得,你所說的不全是真的。」他說話時,眼中閃耀著歡樂的光芒。
幽靈愠怒地反問:「什麼不全是真的?」
「你不是個清白的人,你也不曾盡力行善。我們沒有一個人是清白的,也沒有人曾經盡力行善。上帝祝福你,已經沒關係了。現在不必再追究這一切了。」
名人推薦
康來昌(信友堂牧師)
陳小小(網路作家)
毛樂祈(《小老百姓神學》作者)
約翰•厄普代克(小說家&詩人)
珍•卡隆(小說家)
──鄭重推薦
踏上壯實人生的天堂路毛樂祈
天堂和地獄,其實在生活中就常常能夠有充分的體會。天堂:孩子們彼此扶持、一同玩耍、在簡單的泥土花草上找到興致而開懷,父母得以忙裡偷閒並露出會心的微笑。地獄:轉瞬間,孩子們大打出手,用言語互相激怒對方,父母則抓狂大吼。在工作、生活中,若是處於一個互相信任、互相體諒、彼此支持、無條件被接納的環境,我們彷彿能夠先嚐天堂的喜悅;但在時有爭執、彼此怨懟、勾心鬥角的環境當中,我們對地獄之黑暗、醜陋也多有體悟。
天堂和地獄,似乎不只是生命彼岸的去處,不只是屬於來生,而是現在就可以體會到的真實。
魯益師認為,天堂或地獄是你當下生活的延續。在每個抉擇當中,我們面對了「走向天堂」或是「走向地獄」的抉擇(你無法同時擁有兩者)。尤其,地獄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我們不斷自欺的決定所鑄成的。天堂則是上帝的禮物,但前提是我們要願意回頭。
「朋友,你能不能就只那麼一會兒暫時不想自己呢?」故事中一位光明的靈想要挽回一位不斷自欺的高貴婦人時,說了這句話。
那些持續走向地獄的,其實是自己固執,堅持「想著自己」而不想上帝。那些走向地獄的,是抱持著一種心理狀態──一種把自己刻意隔絕在真實上帝之外的狀態;不願意悔改、不願意停止抱怨、不願意忘卻自己而敞開自己、讓上帝之愛把我們滲透、刺透、剖開。他們為了保護自己不再痛苦、不再受傷,已經為自己包紮一層層的砂布和石膏,心靈表皮也長出一層厚厚的繭,把自己關在愈來愈小的世界中;以為安全、不再痛了,但卻不知不覺把上帝給隔絕了。
其實,我們每一刻都可以回頭的──回到現實(上帝的真實);只是我們太頑固、太自憐、太自以為是(自以為義)、太自我關注、自我悲憫。有時基督徒就像故事中的大主教,甚至更是如此:想傳揚基督教、而從不想著基督;證明上帝的存在,卻從不在乎上帝。我們非常樂於把上帝當作自己所欲求的手段。
在這樣的自我當中,那無法馴服的欲望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就像故事中那隻爬蟲類一樣(在黝黑油滑的幽靈身上的狡猾蜥蜴),牠騎在我們肩上,對我們喋喋不休,應許我們各種虛幻的夢想。牠是我們虛假人生中的共犯結構──「我們要」完成神國大業、「我們要」教會如何如何、看「我」多愛你……。那還是關乎「我」的欲望,那個「我」沒有真正地捨去。
「上帝幫助我、上帝幫助我」這個似乎被爬蟲生物纏累住的黝黑油滑的幽靈,最後竟是故事中唯一獲救的一位。在不斷的掙扎中,他終於願意放手,放手讓神來處置。這樣的放手呼求,卻使他往天堂邁進──開始成為一個新造之人,愈來愈壯實,愈來愈強壯光明;而那隻爬蟲在掙扎中竟也成為一匹駿馬──當欲望被神重新導向,便成為邁向天堂的重要載具。不再是一人(猥瑣之人)一蟲在虛假當中共生、鄉愿,而是一人(新造的人)一馬,雄壯、喜樂地邁向天堂的真實。
魯益師藉著這個故事,提醒我們真實悔改的重要性;不僅是一次悔改信耶穌就拿了天堂的門票,而是每天生命的抉擇,是最基礎、也是最深沉的生命功課。他提醒我們耶穌說過的話:「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或許天堂和地獄不如我們所想像相隔十萬八千里,而是一線之隔、一念之間──當我們棄詭詐而選擇良善,當我們棄苦毒埋怨而選擇接納寬恕,當我們棄自我而選擇上帝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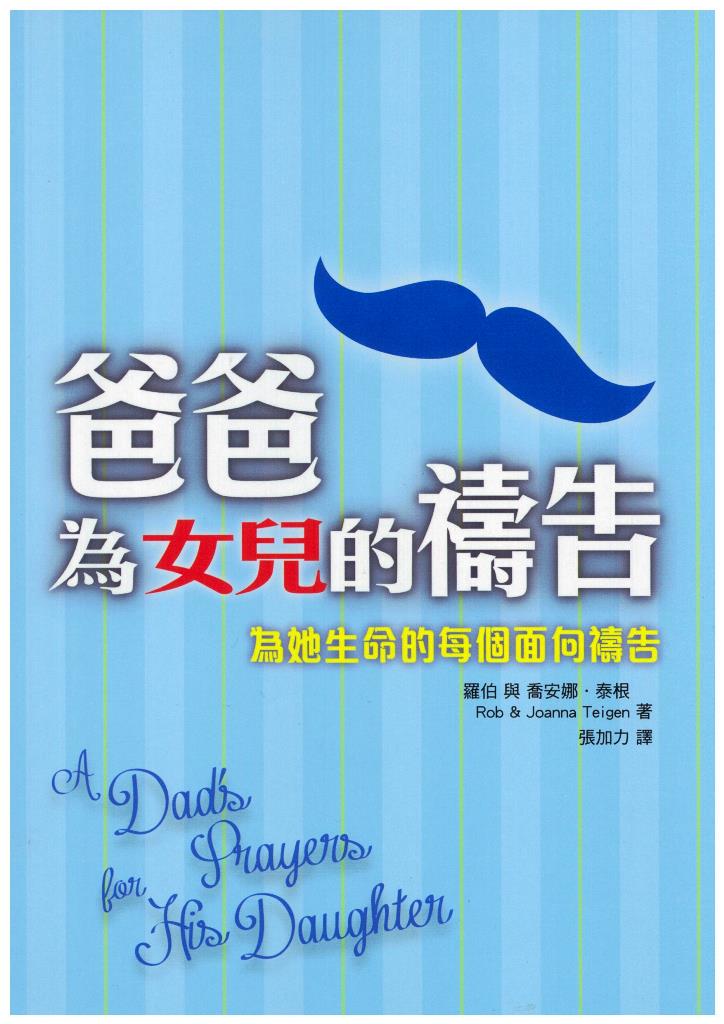
.png)